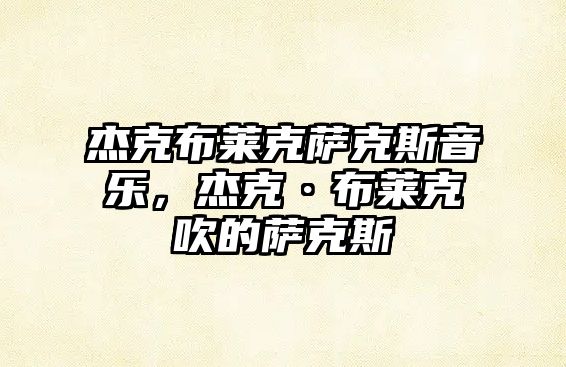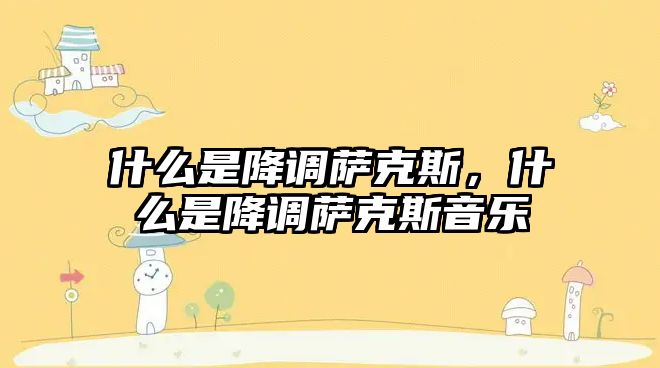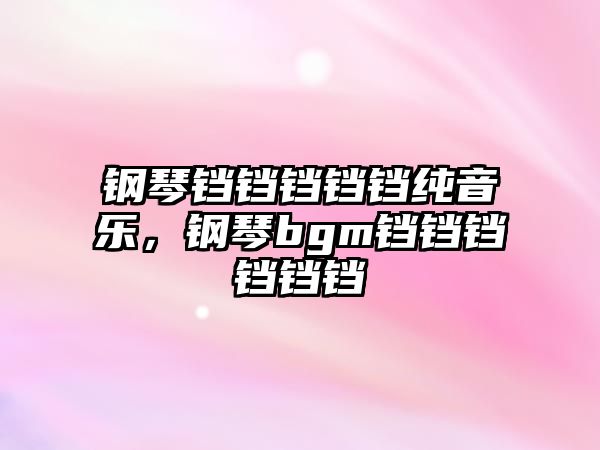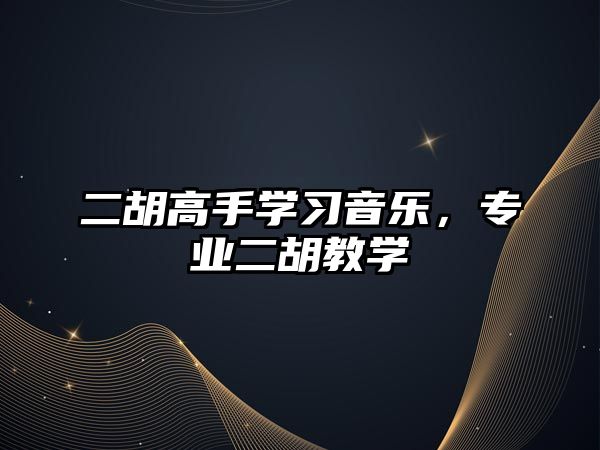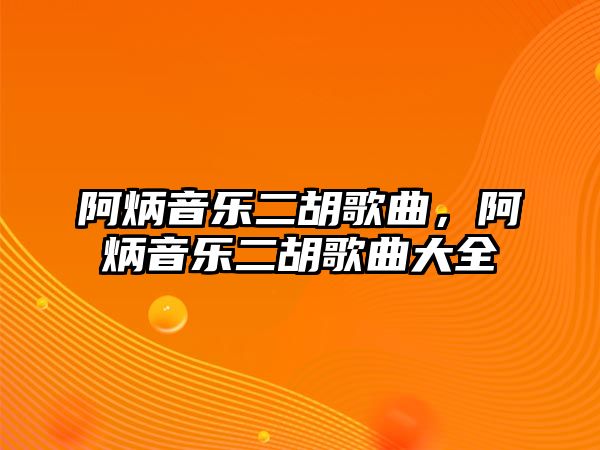小提琴二胡大爺簡介(“任何時候學樂器都不晚” 衢州六旬阿姨的晚年音樂夢)
2019-04-0506:32|浙江新聞客戶端|通訊員吳敏娟
衢州市柯城區興華社區63歲的葉巧仙退休后開始學習樂器,十多年過去了,她學會了二胡、小提琴、中阮三種樂器的彈奏。
阿姨對音樂的熱愛始于孩童時期,卻在老年大放異彩。如今,她每天都會跟著團隊練習、演奏,聽見、看見自己喜歡的樂器依然會從頭開始學,“我會一直彈唱下去,因為我愛音樂。”

啟蒙于知青年代
葉巧仙是家中老三,因小時候喜歡扎六個角的辮子,姐妹們給她取了昵稱:六角。七八歲的時候,她便喜歡唱歌,不論走到哪里,即便是洗澡,她都會即興地來上一段。可惜在窮苦的六十年代,全家人的溫飽都成問題,更不用說學音樂了。即使有天賦,也沒有堅持下去的能力,懂事的葉巧仙自然不愿意給家里帶去麻煩,從未吱聲表達過想學音樂。
1975年,葉巧仙剛滿18歲的那天,“老三屆”知青大姐上調的同一日,她被下放到了航埠龍泉頭大隊。“在公社廣播站當話務員。”雖然知青下放的日子艱難困苦,但是大家總能苦中作樂。“隊里還有學音樂的知青,帶來了小提琴。”葉巧仙看著好奇,討要過來胡亂拉了一通,這也是她第一次觸摸樂器,很是驚喜。為此她把對小提琴和對音樂的期待深深埋在了心底。
五年后,葉巧仙通過考試回城工作。然后就是結婚生子,相夫教子,忙碌的生活擠占葉巧仙所有的空閑,她的音樂夢就此被封存了起來,直到退休。
退休后遇良師
退休后,葉巧仙來到上海寶山區,到兒子工作的地方居住了一段時間。“寶山有一個公園,我會時不時到那里走一走。”有一回,葉巧仙看見有一群跟她年齡相仿的人圍著一張印有《天路》的歌譜,“他們想要學這首歌,可是不知道怎么起頭。”愛唱歌的葉巧仙碰巧會這首歌,受邀唱了起來,那一唱,她“出了名”,變成了教她們唱歌的“老師”,“上海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親近的,可是唱歌卻拉近了大家的距離。”之后,寶山公園藝術團帶著她到虹口表演,“那個場地,真的氣勢恢宏,我往那里一站,心潮澎湃。”
這是葉巧仙遇良師的開端。上海市民中心合唱團找隊員要求嚴格是眾所周知的,葉巧仙也沒有機會去,她只能遠遠地站著聽。說來也是機緣巧合,有一次合唱團練習《醉在草原上》,伴奏壞了,大家都無所唱起,葉巧仙主動請纓說自己會,對方問詢了她來自哪里之后,讓她試了試,沒想到中氣十足的葉阿姨令上海大媽們刮目相看,她才得以進入市民中心合唱團。
進入合唱團后,葉巧仙的歌技越來越好。隨之老師提出了要求,“她說必須學一門樂器,光是唱并不能成為核心,要邊彈邊唱,才能走得出去。”葉巧仙花了200元買了第一把二胡,便跟著老師學了起來。
老師義務教五個學生拉二胡,五個年齡相仿的阿姨,最終只有葉巧仙堅持了下來。“哆來咪發嗦拉系……這是基礎音調,很多人連這個都堅持不下來練習。”葉巧仙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學會了。那時候她還要在外打工,只能抽空學習、練習,但是葉巧仙從未放棄,即便覺得自己學得慢一些,也無妨。學習了個把月,掌握到了基礎知識。葉巧仙又回衢州照顧老伴,只能上海、衢州兩邊跑,一時間也無暇拉琴了。
將幾百首曲子刻在了腦中
2008年,家中事務基本安定,葉巧仙又重拾興趣愛好。“千日胡琴,百日蕭。”二胡是最難拉好的樂器,也是一生都不能放棄修學的樂器。
葉巧仙最超群的是她的記憶力,因為對樂理知識了解甚少,識譜對她來說稍有一些難度,但是她的悟性很高,只要看著、聽著旁人拉兩次曲子,她就能記住一些,回來后再對照著譜子硬記,加以練習,基本上一首曲子三五天便能成形。“其實我只是興趣愛好,實力是不夠的。”如今,葉巧仙的腦子里已經存著好幾百首曲子,不管用小提琴、二胡還是中阮,只要擺好姿勢,悠揚的曲子就能從她的手中傳送出來。

2016年,葉巧仙再次遇到貴人,跟著雙港社區翁老師學習拉琴,“翁老師什么樂器都會,義務教大家。”也就是那時候,葉巧仙聽到了富有詩意,音色恬靜、柔和的中阮發出的美妙旋律,她馬上買來學習。“每個樂器都有各自的音色,我聽見音色迷人的樂器就想學。”她先后學習了中阮和小提琴。雖然每種樂器指法不同,運氣不同,但是葉巧仙很是好學,她肯在一個樂器上鉆研,練好基本功。
姐姐葉瑞仙說,和妹妹一同出門,原本十分鐘能走到的地方,她們往往會花上三十分鐘還不止,“她經常會站在琴行的門口聽別人彈琴,怎么喊都不走。事后還跟我說,她是在學習運氣,就是高音低音的輕重程度。”葉瑞仙還說,妹妹襪子都破了也不舍得買,更換2600多元的二胡卻是眼也不眨一下就買來了。
如今,葉巧仙每天除了家事之外,只要有空閑時間,便跟著三個團隊分別練習。葉瑞仙也在她每天高聲歌唱和不停地練習拉琴的熏陶下,抽空也會跟著她哼上幾句。“她是真的很喜歡音樂,自己唱的歌錄下來再聽,聽到有什么瑕疵的地方馬上改進。有時候,還會因為睡前聽歌興奮而失眠。”姐姐對這個愛唱歌的妹妹是既心疼又無奈,但是她從未阻止過她,“也算圓了她的音樂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