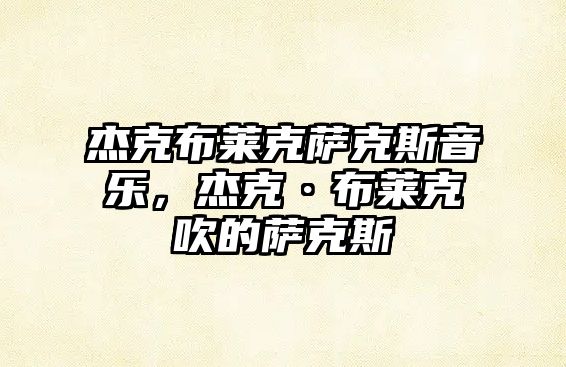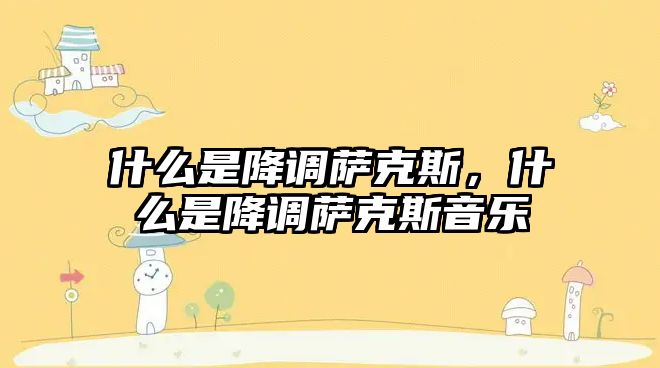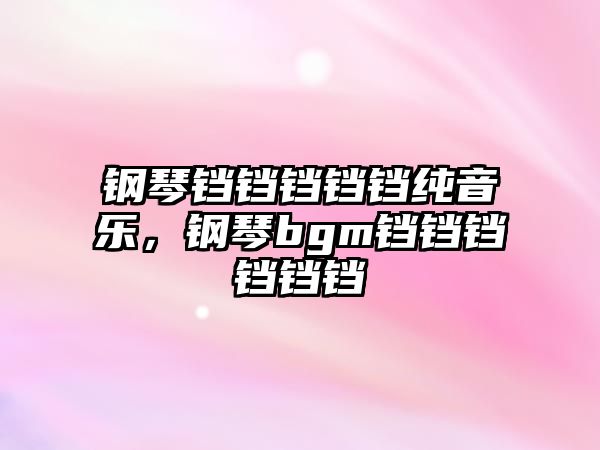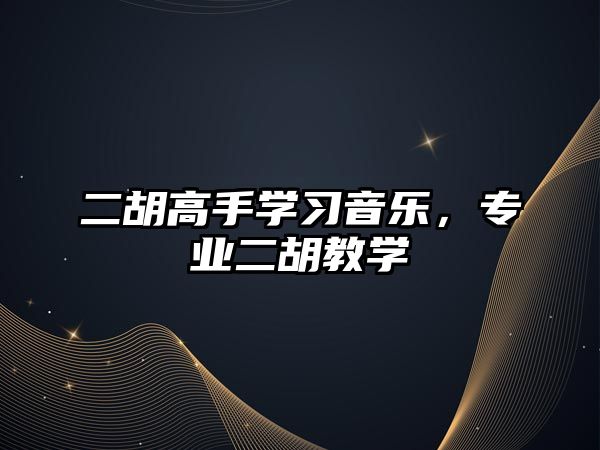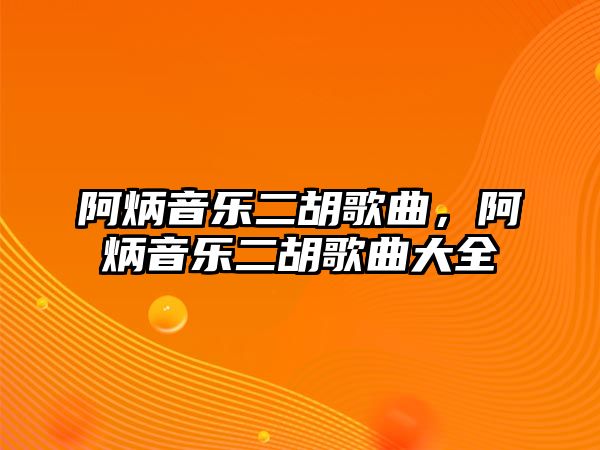二胡演奏蘭陵王(被譽為五千年美男的蘭陵王,留下一曲絕世戰歌,如今成為日本國寶)
無論是魏晉風流,還是唐宋文人,都認為男子要有高雅灑脫的氣質和英俊不凡的外貌。可見,愛美之心自古便有。

縱觀五千年歷史,最受世人推崇的男子共有四位,民間稱其為“四大美男”,他們分別是:潘安、宋玉、衛玠、蘭陵王。
四人當中,潘安、宋玉和衛玠都是白面書生的類型,手無縛雞之力,唯獨蘭陵王文武雙全,戰功赫赫,因此備受人們喜愛,被譽為“五千年第一美男”。

蘭陵王本名高肅,字長恭,是北齊文襄帝高澄的第四子。《北齊書》說他“貌柔心壯,音容兼美”、“風調開爽,器彩韶澈”。《舊唐書·音樂志》則稱他“才武而面美”、“白類美婦人”。但蘭陵王擔心自己俊美的容貌會動搖軍心,于是每逢出征,就用兇惡的面具遮住臉龐,臨陣沖殺,無往而不利。

然而,“自古名將如美人,不叫人間見白頭”,公元573年,年僅33歲的蘭陵王因功高震主,被皇帝賜毒酒鴆殺,四年后,自毀國之柱石的北齊亡于北周之手,高氏皇族也就此湮沒在歷史長河中。
時光荏苒,隨著這段千年舊事留存下來的,還有一首《蘭陵王入陣曲》。
據《北齊書·卷十一》記載,“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邙山之戰,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在《中國人的音樂》一書中,知名音樂學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名譽所長田青老師向我們講述了有關《蘭陵王入陣曲》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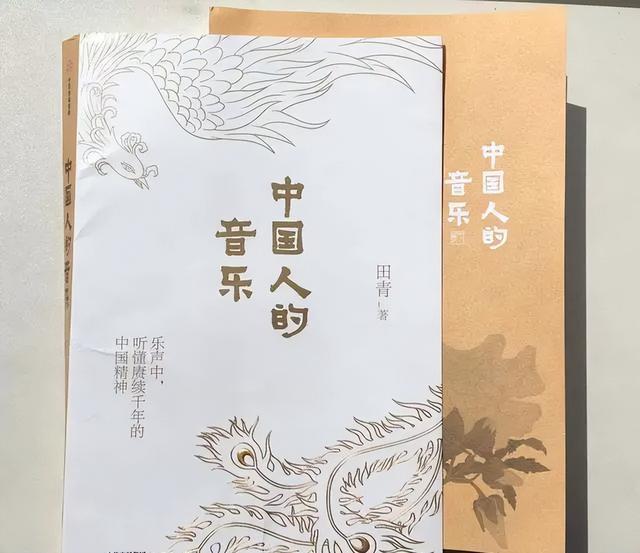
田青老師認為,從音樂形態上來講,《蘭陵王入陣曲》屬于一種古老的盛唐樂種——燕樂。
燕樂也稱宴樂,泛指當時在宮廷或貴族的宴會上所演唱、演奏的音樂,其中包括賭場、獨奏、合奏,大型歌舞曲及歌舞戲、雜技等。這種音樂是大唐繁榮昌盛的象征,也是當時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音樂文化,曾給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諸國以深遠的影響。

然而,安史之亂后,樂工星散,這些瑰麗的音樂之寶只能留存在偉大的中國詩人的記憶力。無論是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還是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都記載了盛唐燕樂的美麗壯觀,也抒發了燕樂衰敗后詩人的唏噓感慨。
燕樂在中國失傳后,卻意外地被日本保存起來。其中,《蘭陵王入陣曲》就是在盛唐時期傳入日本的,至今仍被日本藝術界和公眾視為國寶,是日本國粹“能”之祖。2001年,日本申報的“能”和中國昆曲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為第一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今天,我們如果到日本旅游,還有機會看到這支《蘭陵王入陣曲》,該曲為一人獨舞,表演時頭戴猙獰面具,身穿紅袍,腰系金帶,舞姿一如日本雅樂的特點,緩慢、莊重,儀式感遠勝戲劇情節,所有的戲劇沖突都被弱化,音樂同樣緩慢,甚至帶一點兒凄涼。
在主奏樂器篳篥的帶領下,唐朝廣泛流行的齊鼓、羯鼓、鉦、笙似乎從敦煌壁畫中走了下來,讓我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除了《蘭陵王入陣曲》之外,這本《中國人的音樂》還向我們講述了多種中華傳統音樂,例如古琴與《流水》、古箏與《崖山哀》、二胡與《二泉映月》、佛樂與道樂、《黃河船夫曲》與《東方紅》、《走西口》與河曲民歌、“身土不二”與《我的祖國》,等等。

在這本書中,田青老師將帶著我們聆聽古箏、古琴、琵琶、二胡等傳統樂器的“金聲玉振”,走進南音、佛樂、道樂的神秘世界;領略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民歌的獨特魅力;體會“長亭外,古道邊”“風在吼!馬在叫”“一條大河波浪寬”的時代精神。
通過這本書,我們也會明白,中國音樂究竟好在哪兒、美在哪兒?如何代表中國?如何感受各民族民歌的魅力?新音樂的力量在哪里體現?我們中國人除了西方那套理論,有沒有自己欣賞音樂的邏輯?

總之,中國音樂之獨特,在于其蘊含著一種人文精神,它能觸及中國人心底最柔軟的地方,因此,中國音樂是中國文化沃土中不可或缺的瑰寶和精粹。正如田青在書中所說的那樣:
《詩經》中唱道:“鳳凰鳴兮,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中華民族的子孫是“龍的傳人”,而“龍鳳呈祥”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至境,象征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個夢想實現的過程中,中國人的音樂也將隨著鳳凰之鳴,聲播世界,樂動人心,和合天下,萬福同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