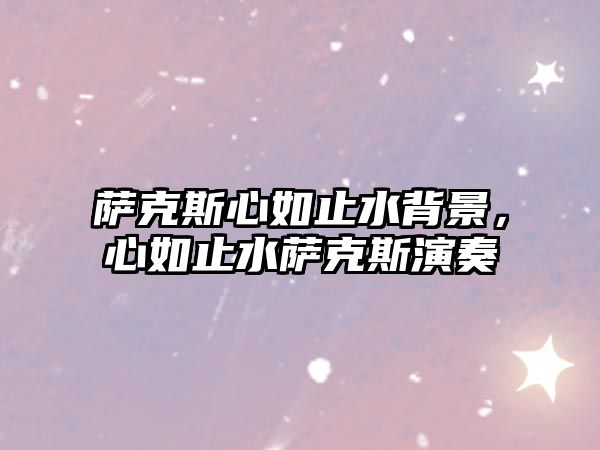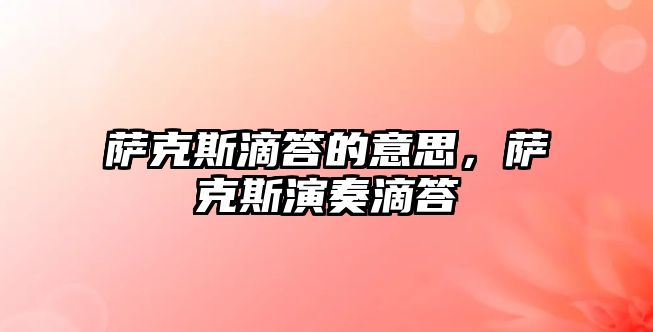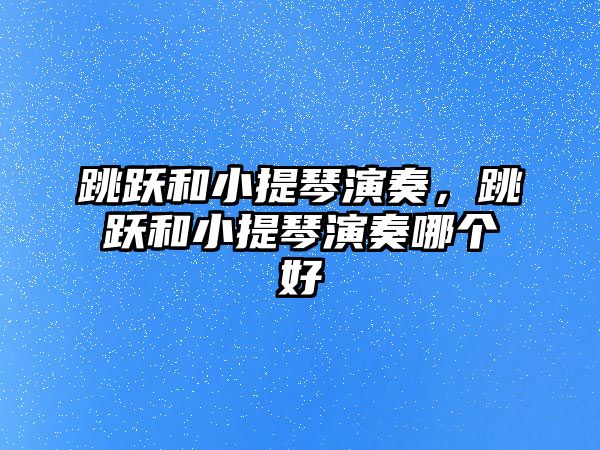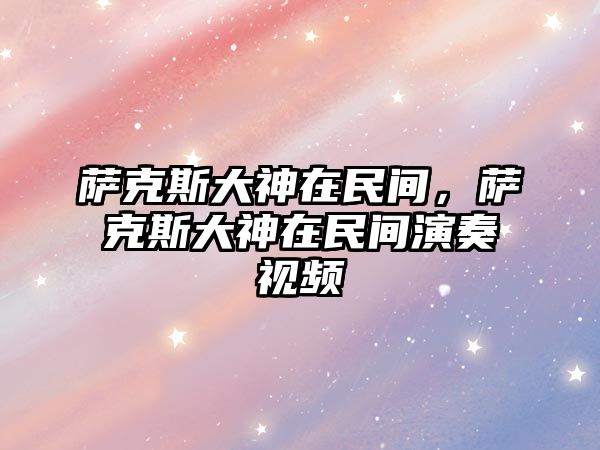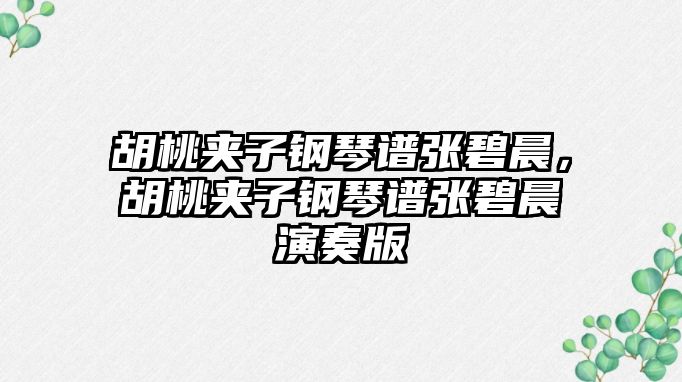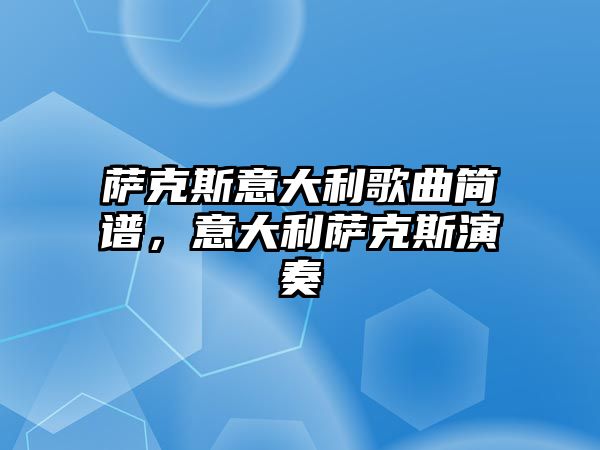動作夸張二胡高手(二胡演奏高手有氣功,你永遠都想不到)

觀看演奏二胡是遵循人體生理、心理活動規律所進行的一種特定形式的合目的、合規律的藝術實踐。這種藝術實踐與傳統文化氣功一脈相同,如氣功中的三要素調身、調息、調意,很適合于二胡的演奏和訓練,因為此三者正是與演奏的姿勢、呼吸、心態等一系列重要內容相關。
調身,就是按一定的規范調整好演奏姿勢。筆者將坐的演奏姿勢概括成十二字訣:腰要直、目要平、肩要松、氣要沉(氣沉見調息)。重點是腰要直。從生物運動力學的角度講,腰是人體運動的主軸,在神經系統支配下,人體旳靜態姿勢靠腰支撐,動態靠腰支撐和帶動。演奏前坐穩后通過意念把十二字訣默念一遍,借以調整好演奏姿勢。默念或想象就是調整。否則若調身不佳則會導至演奏者找不到最適宜的內部感覺(如動覺、平衡覺等),甚至造成生理、心理障礙,影響演奏。
調息,即用意念調整呼吸。演奏者有三種呼吸狀態:自然呼吸狀態、演奏前經調整的呼吸狀態和演奏中的呼吸狀態。自然呼吸狀態根據呼吸生理機制,通常分為三種型式:腹式呼吸,主要是膈肌和腹壁肌的收縮和放松。胸式呼吸,主要靠肋間肌的收縮和放松。但實際上沒有絕對的腹式呼吸或胸式呼吸,而是混合式呼吸,也就是所說的自然呼吸。演奏前調整的呼吸狀態,即氣要沉。在傳統演奏美學中一向認為調整呼吸對于演奏至關重要,所謂“一在調氣,一在練指”,“調氣則神自靜”,神靜才能開展想象,進入境界。

如何調整呼吸?可采用氣功中各種調息法,如順呼吸法(用鼻呼吸,如聞香花,吸氣時以意領氣至丹田或下腹部,漸鼓小腹,呼氣時漸收小腹)、意守法(自然呼吸,呼氣時意守丹田,吸氣時不意守)等。氣功的調息法是以自然呼吸為基礎,但又不同于自然呼吸,首先它強調意念的引導作用,這說明呼吸是一種反射現象,通過第二信號(意念)是可以調節其呼吸部位、呼吸節奏和呼吸深度的。與自然呼吸相比,演奏前用氣功調息法調整的呼吸,顯得更深沉、更平穩和較緩慢,它可使演奏者意、氣、神相合,收到平心靜氣,神閑致遠的效果。演奏中的呼吸狀態。演奏中的呼吸是在自然呼吸的基礎上,通過長期演奏實踐所形成的同演奏活動相適應的呼吸動力定型。這種定型能把相應肌肉群的活動同呼吸器官和心臟等器官的活動統一起來,在進行調節時,由大腦皮層的系統性活動所統一起來的內外感受器的神經沖動都參加了活動。
概括的講,演奏中的呼吸具有無規則性和有規則性兩個特點。演奏中的呼吸由于受音樂內容、節奏、力度、速度、演奏技法等多種因素所制約,其呼吸節奏要適應演奏的需要而不斷變化,一般是吸氣較快而呼氣較慢,有時還要搶氣和屏息。因此與自然呼吸相比,具有明顯的無規則性。另一方面,在人類的肌肉活動中,呼吸和形態動作的開合、展收、松緊、起落有密切關系,一般是開吸合呼、展吸收呼、起吸落呼、松吸緊呼等,這也是定型。如手臂上舉一般伴隨著吸氣,下落時伴隨著呼氣。二胡演奏一般也遵循這個規律,吸氣往往趕在拉弓上,呼氣趕在推弓上。一首樂曲可分為若干樂句、句逗,而吸氣往往趕在樂句的聯接處或句逗處,有時利用休止符吸氣等等,這是呼吸與語言聯系的經驗在起作用。此外,氣息流量又往往與表情有關,如演奏激情旳樂段,氣息流量則要大些,相反,若演奏緩慢、深情柔美的樂段,氣息則相應的平和些,這是呼吸與情感聯系的心理經驗在起作用。以上兩條都源于生活和藝術實驗,所謂“道法自然”。在藝術處理中注意呼吸與音樂內容及演奏動作有機聯系,是提高表現力的重要條件。這就是演奏中呼吸狀態的規律性。

調息的另一層含意是指氣功中所說的“氣”在演奏中的運用,氣功中的“氣”一般是指由意念的引導而發生的一系列生理、心理效應,主要是指意念、氣息和肌肉活動之間的內在聯系,如在演奏時要意、氣、力、形(動作)、聲相合,并且要做到以意領氣、以氣發力。如此演奏的效果才有生氣。調意,氣功的調意是通過觀想或想象來排除雜念,凈化意識,進入氣功態。如觀想日、月、山、河、花草樹木等。調意在演奏中也是為了排除雜念,并通過想象或意像進入特定的演奏境界。如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偉在演奏悼念周總理的樂曲(思念)時,感到眼前是一片藍色,是一種非常肅穆的氣氛。而當演奏比較喧鬧的(鳥投林)時,感到眼前突然是一片紅色,是一種熱烈歡躍的氣氛。再如著名二胡演奏家閔惠芬在演奏(江河水)的第二個樂段時,心中似乎看到了(祝福)中祥林嫂臨死前的情景,那氣氛是那樣的麻木、茫然、凄慘。筆者認為演奏是綜合性的心理過程,很難用語言作詳盡的描述,那是一個朦朧意境。但從宏觀上是把握,有三個重要方面值得研究。
一是積淀,二是同構,三是動力定型。此三者在時空焦點上的顯現便構成了演奏時的心理定勢。積淀包括先天的所謂集體無意識和主體后天的一切經驗,如對傳統文化的積淀。對大千世界的靜態、動態、節奏、張力感知的積淀。對人類情感活動的積淀。對藝術實踐的積淀。需要強調的是對民族語言的音調和語調的積淀,對演奏藝術來講,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尤其是漢語,它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最富有音樂性和表現力的語言之一。我們知道語調變化是心理活動的反映,它具有很強的表情、達意的作用。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線性的音樂藝術,是源于民族的語言。因此,筆者認為民族語言中的音調(如平、上、去、入),由于各個地區的調值不同,是構成不同音樂風格的基礎。而民族語言中的語調,如重音、停頓和平升曲降,不僅是語言藝術中表達思想感情的三張王牌,同時對于民族語態的積淀,具有特殊的意義。它幾乎含蘊著全部演奏美學和演奏心理學的真諦。積淀是形成主體文化心理結構的基礎,是藝術創造的信息庫。

同構論是引進的學說,來自格式塔心理學派。但在中國這種思維方法其歷史則更加悠久,那就是產生于原始母系氏族社會時期的卦象思維。古老的八卦“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得出了陰陽的判斷。于是把天、地、人在陰陽的前提下統一起來,把人與自然并提,并指出人與自然的內在關系。這就是同構,也是對自然的人化。陰陽相推,變在其中,相輔相成,剛柔相濟,比張力或定形的提法,則顯得更加辨證。卦象思維是重在理性,重在對自然本質及其變化的把握上,重質象而不重表象,重意而不重形,觀象可以見義。這種設象見義的表現方法,奠定了中國民族藝術的美學表現基礎和民族的審美意識基礎。于是中國詩講究立象盡意、情景交融,用比、興而導出情旨。中國戲劇是具象的,但它絕非是生活中實象的寫生,而是通過質象性的具象符號來達到表現力與形式美的統一。使觀眾賞其意、領其神、感其韻。中國畫則更是重在神似而不求形似。中國的音樂和書法雖然有視、聽之別,但它們都是借助線性的質象來表現情致的。借質象來表情,于是含蓄備至,可意會不可言傳,可悟而不可得。“高山流水”的提法從同構的觀點看,實際上可以解釋一切樂曲,因為可以說有各質象不同的高山流水,于是它能含蓄表現不同的情致,歸根結底仍是陰陽變化。

關于動力定型。筆者曾對數十名演奏家作過心理調查,題目是“演奏時你心中在想什么”,有人回答在樂曲標題的提示下,心中似乎被一種難以言狀的朦眬意緒所籠罩。有人說有時會時隱時現產生某種意象。有人說演奏時心里也在唱,心中唱得有味兒手上拉的才有味兒(這是戲曲界琴師的說法),甚至說“三分拉,七分唱”。有人說演奏時主要是能感覺到各種不同的“范兒”(勁頭兒),如剛、柔、輕、重、急、緩、抑、揚、頓、挫等等,有時為了“起范兒”(表現某種勁頭兒),心中先要有所預示。有人則說不出演奏時心中在想什么,似乎練熟了,一切都是順其自然。這就是說凡成熟的演奏,大抵是通過直覺來掌握的,即所謂動力定型。伴隨著動力定型,演奏者的心態往往有一種強烈的表演欲望,同時“藝名人膽大”,甚至有點兒自我陶醉或自我欣賞或物我兩忘的味道。然而動力定型并非完全排除意識的參與,如藝術上的夸張、演奏中的分寸感或音準稍出偏差時迅速的作出校正,都說明意識在起作用。不過這種參與是簡約的,類似氣功中的“意守”,那是似守非守,而不是“死守”。演奏中的意識活動也是如此,似守(意識),則有意夸張,推波助瀾,非守(下意識),則隨波逐流,莫知其然而然。
積淀、同構、定型此三者在演奏中是如何體現呢?筆者體會關鍵在于意念先行。意念先行意味著“意”是演奏活動的先導,即以意領氣,以氣發力。同時還意味著根據“體曲之意,悉曲之情”,打開積淀的信息庫(或激發積淀的經驗),從而產生想象、意像、感情、意緒。總之,形成一定的氛圍,在自動化的條件下,通過特定的氛圍與音樂運動的同構關系,化為線性的音樂質象,借以表現情致,而這種轉化或質像,幾乎是在下意識中通過直覺來把握的。所以說只能心領神會,而不可言表。

琴友們,如果你們有什么見解,歡迎通過下面的評論區評論,同時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樂有群。一起討論、一起進步、一起成長吧!(進群微信:minyuelao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