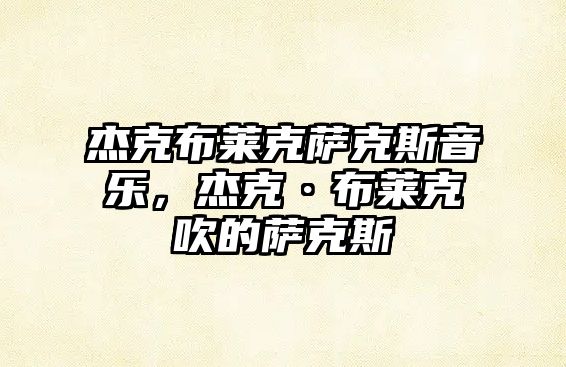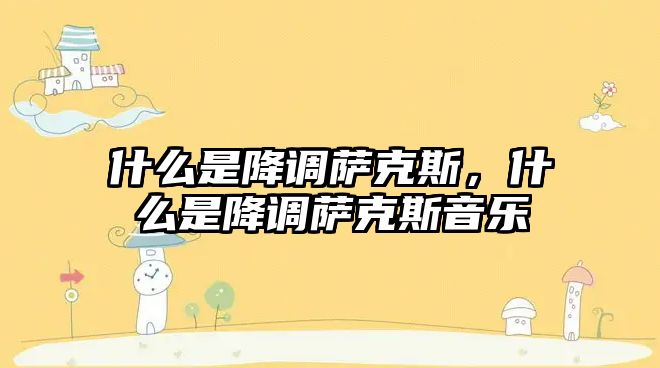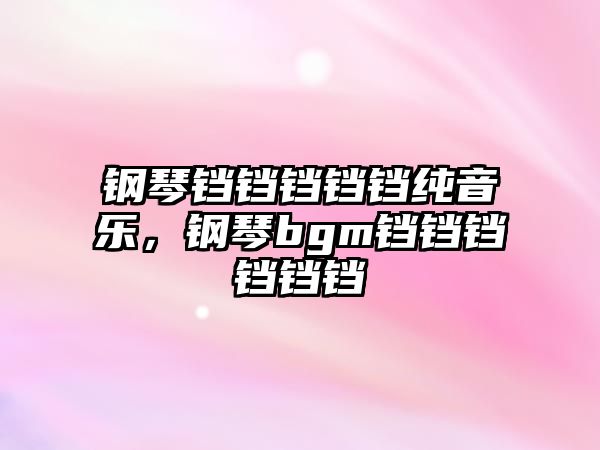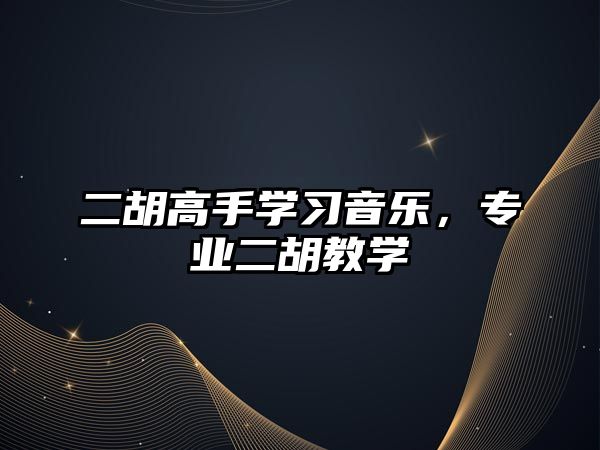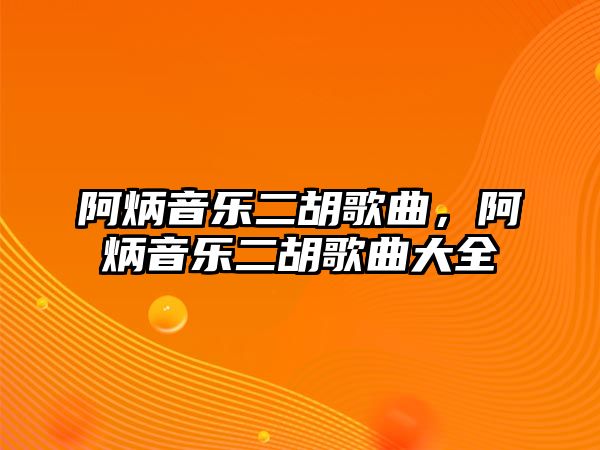拉二胡的功夫音樂是什么(周星馳《功夫》中的“漁歌”,是這位作曲家60年前的成名作)
11月29日,古琴演奏家龔一、琵琶演奏家吳玉霞、笙演奏家翁鎮發將在上海音樂廳攜手上海民族樂團,為觀眾獻上一場藝術盛宴。
這場音樂會的多首作品都出自同一位作曲家——顧冠仁。79歲的他,也將親自上臺指揮。
作為上海民族樂團終身藝術顧問,顧冠仁在60年的時光里寫下了許多經典民樂作品,是當代中國民族音樂發展的親歷者與見證者。
從17歲的“漁歌”,到70歲的“暢想”
1959年,年僅17歲的顧冠仁第一次來到舟山漁港采風。生于江蘇海門的他,從小在長江邊長大,卻是第一次踏上漁船,與漁民們一同出海。
這是一次豐收的旅程,漁民們唱著勞動號子,在與風浪的搏擊中收獲了來自大海的滿滿饋贈。節奏有力的勞動號子和舟山民歌,深深打動了顧冠仁。回到上海后,他與作曲家馬圣龍合作寫下了民樂合奏曲《東海漁歌》。漁民戰勝驚濤駭浪的情景,以及豐收歡樂的場面,被鑼鼓、嗩吶等民族樂器演繹得十分生動。
60余年過去了,這首充滿生活氣息的作品至今仍是許多民族樂團的保留曲目之一。顧冠仁與馬圣龍更想不到的是,這首曲子還被導演周星馳選中作為電影《功夫》的配樂,隨著影片一起“聲入人心”。
2012年,古稀之年的顧冠仁又一次寫下了一首與大海有關的作品《藍色暢想》。旋律中的藍天、白云、碧海、波濤,引發聽眾的無限遐想。這是一首寫給青少年的音樂,顧冠仁希望年輕人能定準航標、乘風破浪。
從17歲寫下充滿民間風情的小曲,到70歲寫下充滿現代風格的民族管弦樂作品,顧冠仁一直在民樂創作的天地中求新求變。
顧冠仁至今記得小時候第一次聽到琵琶曲的感動。“我家鄰居是當時江南絲竹界小有名氣的樂師瞿東森。他琵琶、笛子、二胡樣樣精通,經常與學生們在家中一起演奏。我當時就覺得民樂太好聽了。”在瞿東森老師的影響下,顧冠仁開始學習琵琶。1957年,他考入上海民族樂團擔任琵琶演奏員。《東海漁歌》《京調》《三六》這三首作品的創作,讓他脫穎而出。樂團決定讓他專攻創作,去上海音樂學院正式學習作曲。
在上海音樂學院,顧冠仁除了上課就是泡在琴房或圖書館,他潛心學習作曲、復調、作品分析、管弦樂配器法等課程。1965年,他回到民樂團,沒想到等待他的是長達十多年的創作空白期。在那段漫長的日子里,他研究唐詩宋詞,鉆研民歌資料,并利用借調上海滬劇團、上海京劇院的機會學習戲曲音樂。這對他后來的創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78年,上海民族樂團復團,顧冠仁終于盼來了創作的春天。僅1979年一年,他就創作了兩首較有分量的作品:琵琶協奏曲《花木蘭》和民族管弦樂《春天》組曲。此后,他的民族管弦樂《將軍令》、古箏與弦樂隊《山水》等作品常演不衰。近二十年來,顧冠仁又奉獻了大型民族管弦樂《八音和鳴》《歲寒三友———松、竹、梅》以及曲笛與古箏雙協奏曲《牡丹亭》等知名作品。如今,已近79歲高齡的他,依然筆耕不輟。
在上海民族樂團團長羅小慈看來,顧冠仁的音樂總在思考古往今來的人生哲理,尋覓地域風情和自然風光。他的藝術深扎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肥沃土壤,融入民間音樂的多彩神韻和豐富智慧。

2019年10月顧冠仁在《敦煌之夜·藍色暢想》作品音樂會上致辭
讓新江南絲竹,走出“八大曲”的套路
音樂評論家劉再生曾用“濃妝淡抹總相宜”來形容顧冠仁的音樂。他的作品深受江南絲竹的影響,流淌著細膩流暢的江南風韻。
1985年,顧冠仁參加《中國民族器樂集成》(上海卷)的編纂工作,在6年時間里對上海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深入的調查、收集、整理和錄音,隨之對江南絲竹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顧冠仁告訴記者,江南絲竹流行于江蘇、浙江、上海,以典雅、細膩、流暢、委婉著稱,是秀美的江南山水及善良純樸的江南人民性格的生動寫照,也是我國民族音樂中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間樂種之一。江南絲竹的形成和發展與其特定的地理人文環境及海派文化善于吸收其他藝術品種、博采眾長等特點息息相關。
20世紀初,江南絲竹逐漸形成了“八大曲”,即《中花六板》《慢六板》《三六》《慢三六》《四合如意》《行街》《云慶》《歡樂歌》八首樂曲。
1961年,19歲的顧冠仁做了一次大膽的嘗試,將“八大曲”之一的《三六》改編為彈撥樂合奏。在保持其傳統旋律架構的基礎上,加大了不同樂器間的反差力度,增強了節奏的松緊變化,充分發揮了各種彈撥樂器的特色。這首改編版《三六》既保持了原曲的韻味,又給聽眾帶來了新的感受,至今仍是中央民族樂團、上海民族樂團等多家樂團的保留曲目。
江南絲竹有著細膩委婉之美,但長期以來也存在著音樂語匯較為單一、貧乏的問題。有些傳統曲目是同一“母體”的變體,在演奏中甚至容易出現“串曲”的現象。“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就在于不同曲目或不同段落中的共性太多,缺乏個性。如何加強樂曲的個性,是賦予江南絲竹新生命的關鍵。”顧冠仁坦言。
20世紀80年代,顧冠仁開始了“新江南絲竹”的探索。1982年的《春暉曲》在保留傳統江南旋律特色的基礎上,糅進了滬劇中“基本調”長過門的音調及二胡的演奏特色,極富個性。2012年的《東灘晨曲》描寫的是崇明東灘鳥類自然保護區的晨曦。顧冠仁借用了西安鼓樂的表現手法,用大、小鈸模擬鴨子嬉戲的情景,把崇明“非遺”項目“鳥哨”演奏加入樂曲中,使音樂形象而逼真。

對話
“國潮”要成為經典,還得靠好作品
上觀:您多年來致力于“新江南絲竹”的創作,“新江南絲竹”與傳統的江南絲竹相比,有哪些變化?
顧冠仁:江南絲竹有著一百多年的歷史,是江南文化的一部分。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欣賞習慣在不斷變化。傳統江南絲竹單線條的旋律以及單一的調性已不能滿足人們的欣賞要求了,必須求新求變。新江南絲竹所表現出的時代氣息與過去不一樣。在創作手法上,增加了音樂的對比度,節奏模式也變得多樣化。和聲、復調的運用在傳統江南絲竹中也是沒有的。
但是,不管怎么變,韻味不能變。這種韻味也許很難用語言描述清楚,是一種音樂感覺。寫新江南絲竹音樂,必須對這一民間樂種有深入的了解與感情,掌握它的特點。
上觀: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作曲家將民族樂器融入交響樂的創作,您怎么看這種現象?
顧冠仁:民族樂器與交響樂團的合作,是一件好事情。能否真正產出好的作品,前提是作曲家對民族樂器的性能、特色,以及樂器之間的共鳴要有深入的了解。有些作品雖然預想的效果很好,但最終的呈現卻不盡如人意。每件民族樂器都有其獨特的性格與音樂語言,作曲家要懂得揚長避短。不要把二胡寫成小提琴,更不要把古箏不當古箏,敲敲打打,一句旋律都沒有。旋律是體現民族樂器特色的重要手段。
上觀: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相比,似乎更注重旋律?
顧冠仁:中西方音樂盡管文化底蘊不同,但西方音樂也重視旋律美,兩者也有相通之處。西方音樂的和聲發展得比我們早,這一點值得民樂學習。
我認為,不論是哪個地方的音樂,都要表現美,表達情感,而表達情感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旋律。民族樂器即使只有一把二胡、一支笛子也可以把情感表達得很充分,就是因為民樂非常重視旋律。因此,民樂創作的旋律不能丟,在此基礎上,各種音樂手段都可以為我所用。比如我在寫《牡丹亭》時,為了營造夢境般的音樂效果,采用了12音的和聲,非常現代,但這種技法的運用與旋律并不沖突。
上觀:近年來喜歡民族音樂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他們把一些新穎的民樂演奏形式稱為“國潮”。您認為民族音樂今后該如何吸引更多的觀眾,保持生命力?
顧冠仁:民樂的表現形式其實是豐富多樣的。大型民族管弦樂隊這種形式的音樂表現力很強,要繼續發展。與此同時,小型多樣的樂器組合或者小型重奏也是民樂的傳統。
上海民族樂團等不少民樂團近年來都在探索新的表演方式,運用多媒體為背景,或者讓演奏員穿上古裝等,這都是很好的探索。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音樂本身,只有優秀的作品才能真正留住觀眾。
現在有很多年輕作曲家都在努力,希望他們能夠把傳統的民樂精髓與現代的作曲手法很好地結合起來,既借鑒西方作曲技法,又充分發揮中國音樂的韻味之美,尋求民族音樂的時代表達。
欄目主編:龔丹韻文字編輯:陳俊珺題圖來源:上海民族樂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