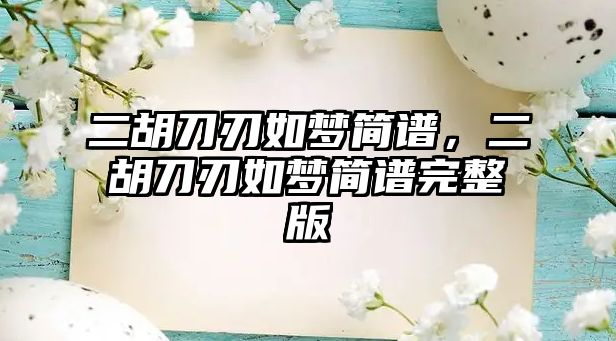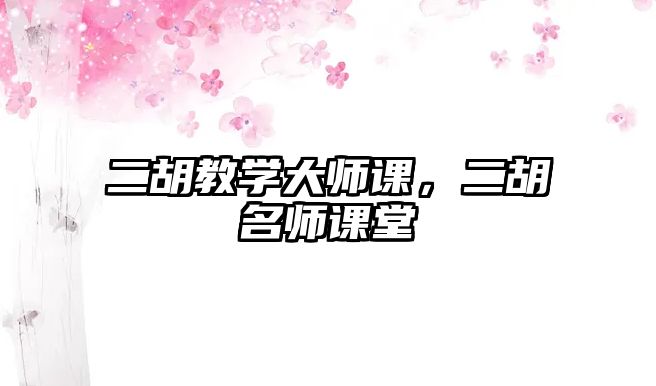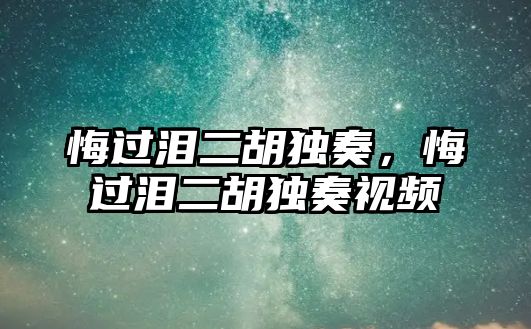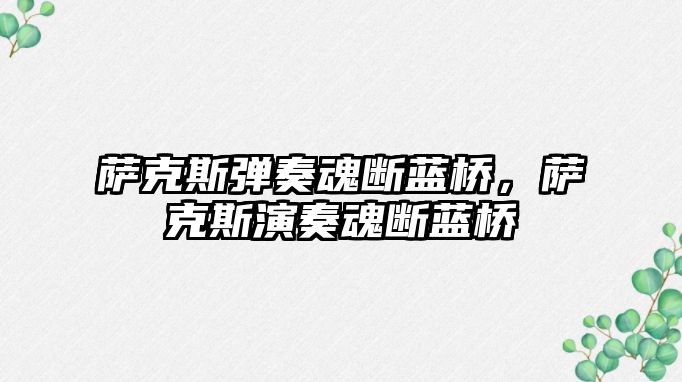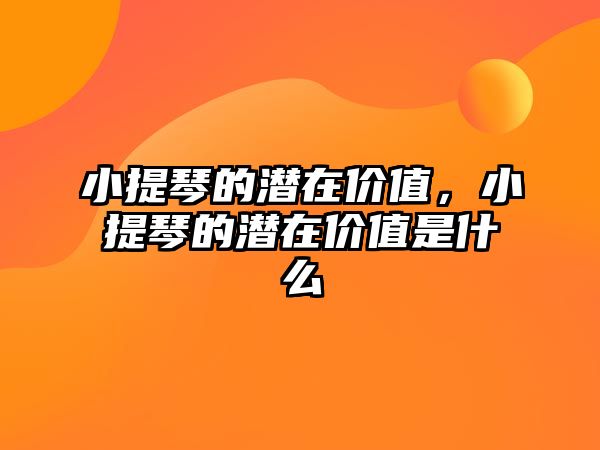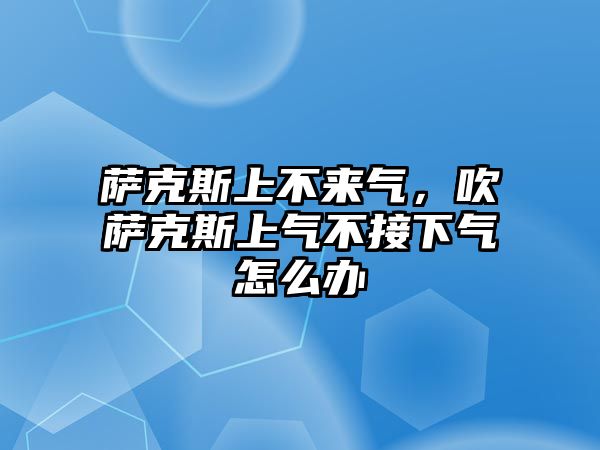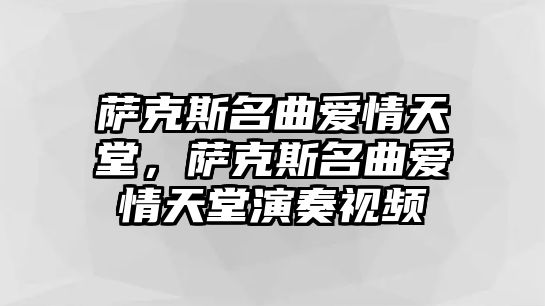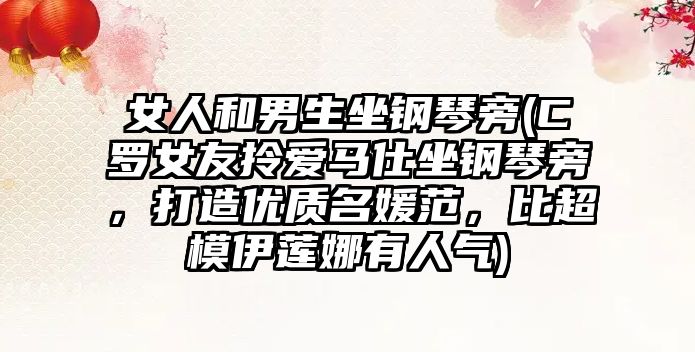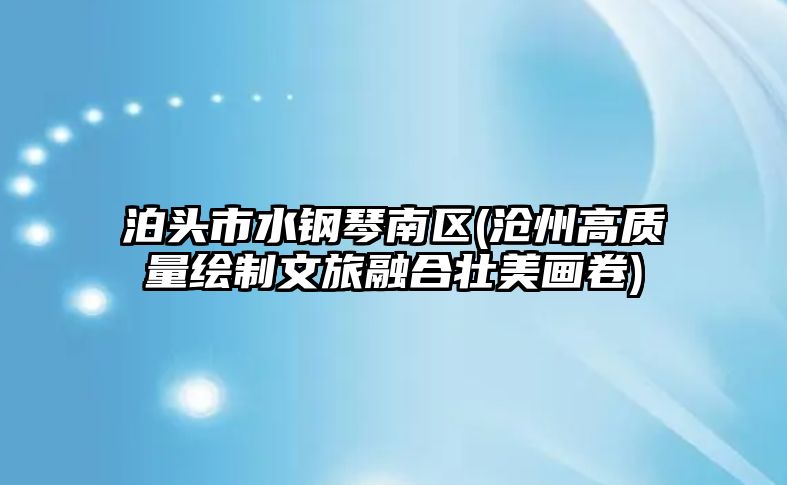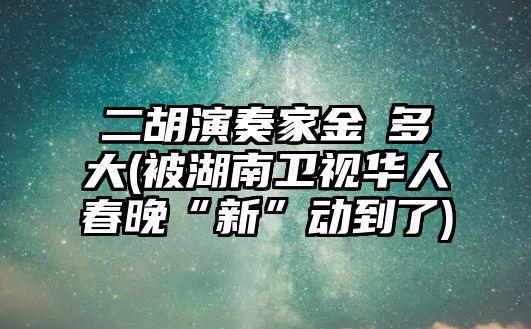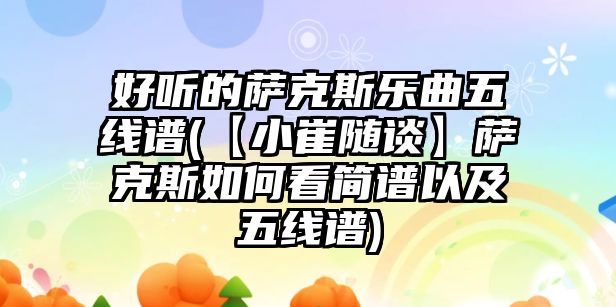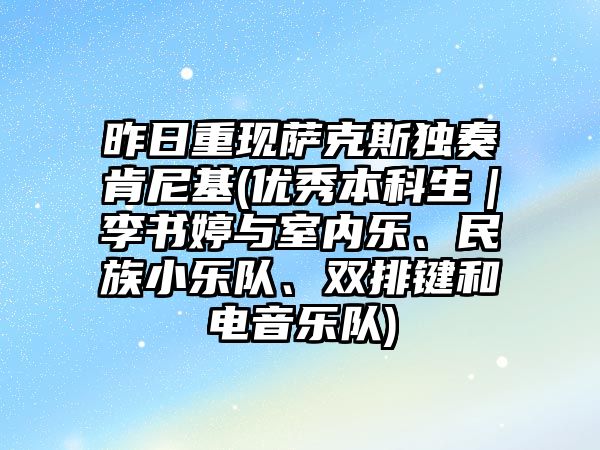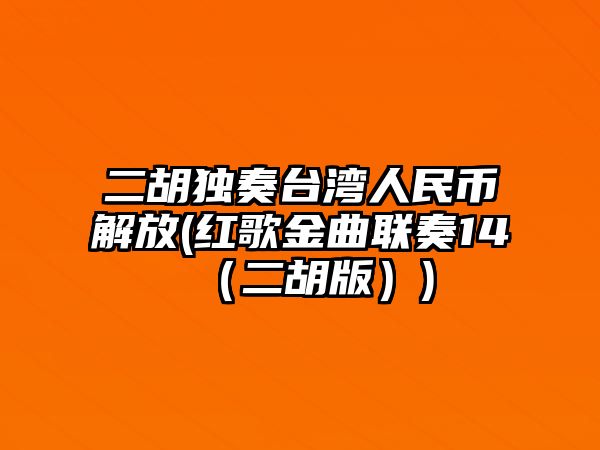二胡弟弟是什么玉石(承載記憶的二胡)
一
我幼習二胡。
疏簡的琴桿木筒,搭上二根弦;蛇皮因為常年的共鳴震顫已然變得緊薄透亮,琴桿在漫長的歲月里與人的手掌相互打磨,終現出濕潤如玉石的光澤與觸感。馬尾弓一抖,獨屬于松香的微苦微甘的氣息便在空氣里無聲彌漫。腕間一個折,指尖抹復挑,弓尾的顫音帶出哀婉九曲的詠嘆,像根極細的絲,哀婉九曲地縛住人的心臟。掙脫不開,只能隨著拉琴人的手腕迂回而遷移。
更多的時候,二胡承載的是記憶。

琴聲一起,琴聲便紛至沓來;老屋厚重的木門吱呀開啟的聲響,雕花大床床頭,被兒時的我摩挲了無數遍的纏枝連紋,還有那些午后靜默的,無聲流動的光陰。《二泉映月》其實是最簡單不過的曲子,爺爺卻從不肯教我。他總是悠悠地搖著蒲扇,以一種唱歌般悠長地聲音嘆:“太浮啦…太浮了。拉琴,心要靜……”
偶爾的暢意滿懷,他也會自己坐在院子里拉一段曲子。袓父的手是真正暮年人的手,黝黑,粗礪,掌心印滿黃土地上的溝壑。然而當它們奏起胡琴的時候,又會瞬間變得如此靈動。

猛然想起去年最后一次聽他拉琴時的光景。
袓父闔著眼。
月華從空中傾瀉下來。
月華從他的指尖傾瀉下來。
院子里桃花開了滿樹,灼灼其華。

二
前些日子,接到朋友從塞納河畔寄來的信。寬寬大大的信封里空蕩蕩;一朵風干了的不知名的寶藍色小花,一方純白色的手巾,一張小小的卡片,除此再無其他。那個有甜美酒窩的女孩還是那樣小資又文藝,在那張卡片上,深藍的墨水娟秀地寫:
你總說/鋼鐵城市里沒有明月/我本想撕一瓣予你/卻只能/贈你一方浸滿了月光的布/一段浸滿了月光的塞納河/是否能記起兒時背的詩/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我將那方帕子擱在了枕邊。忍不住地想像千里之外的那個活得淡定美好的姑娘,是怎樣用它兜住了異國的明月,又怎樣用指尖沾染上的月華寫下這明月一樣的句子。忽然覺得,香車豪宅,皆不及這一明月。

三
晚自習結束時,出來得有些晚,人流已經幾乎散盡。乍暖還寒的天氣,夜風里行人的面龐都是淡漠,月光下面,他們的影子行色匆匆,張牙舞爪,像是欲望的怪獸在趾高氣揚。我突然不想騎車,只靜靜地推著走,月亮格外明亮,在我的頭發上,肩膀上跳躍、憩息。我怔怔地停下步子,怔怔地朝它伸出手去。
家中的二胡已經蒙塵,而這樣的月光亦和我久別未逢。瞬間有種力量在四肢百骸里流淌,我甚至可以看見指尖在散出清朗的月華。
心中無所有,唯有滿懷明月相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