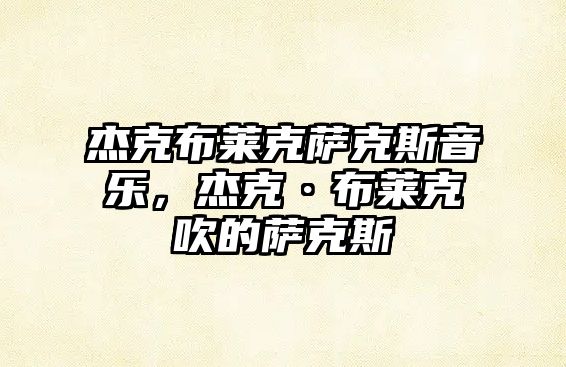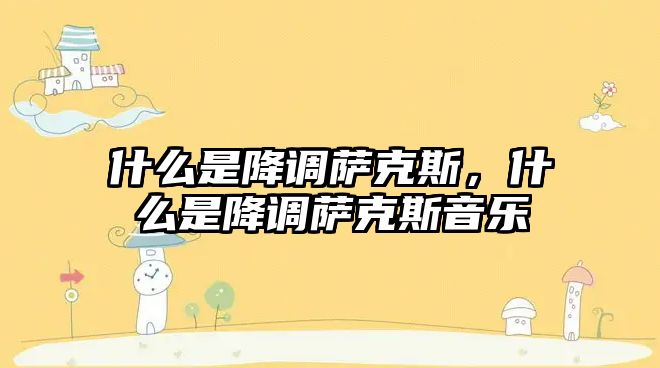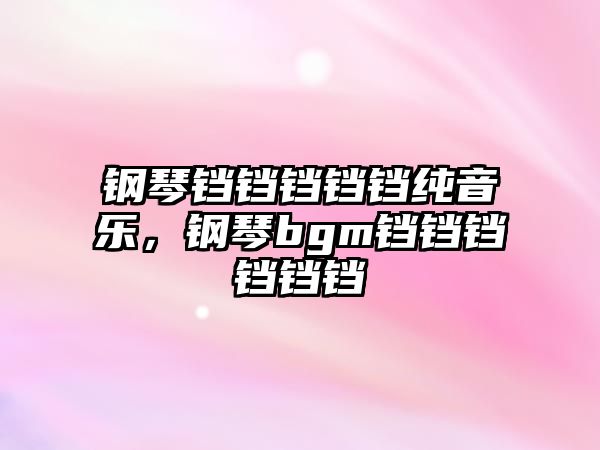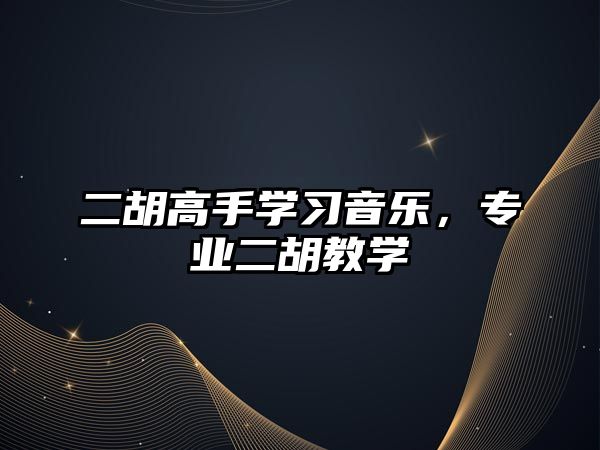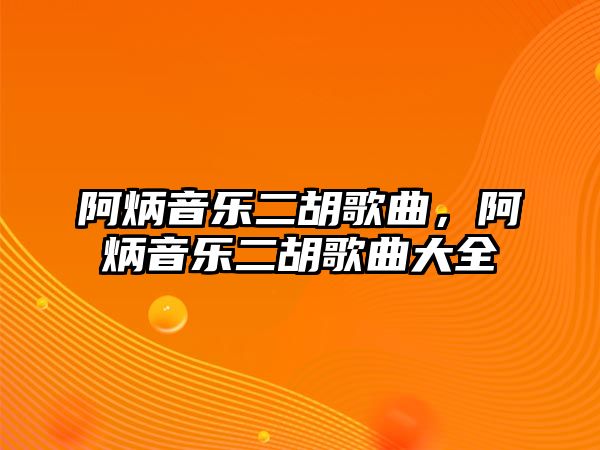小提琴定價方案(既然藝術品總是被明碼標價,我們又該如何為一首音樂“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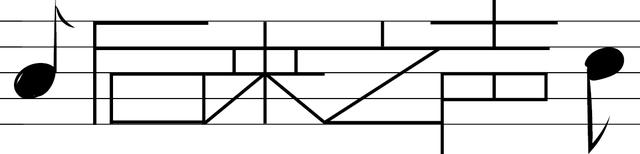
任何一個時代,都充斥著大量“廉價”的音樂,對于當時的民眾來說,自有其存在價值,能夠滿足人們的現實需求。某些“廉價”的音樂作品,有朝一日甚至會變得“高貴”起來。
被量化的創造力
廉價的藝術究竟指的是什么?在繪畫和雕塑等領域,“廉價”這個詞很容易理解。藝術品通常都會明碼標價,即便那些珍藏于各大博物館的無價之寶,其實也已經代表了一種價格。
很多人對藝術品的過度商業化感到擔憂,比如法國當代哲學家馬克·杰木乃茲在評價阿多諾的藝術理論時談到:“阿多諾的悲觀在于藝術所無法逃遁的宿命,代價昂貴的藝術獨立性,掉過頭來與藝術相對立。”說到底,“藝術依舊會踏進商品的圈子”。
但藝術品市場畢竟具有悠久的歷史,公眾對歷史上最重要畫家的評判標準,也很難完全脫離其作品的拍賣價格。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該現象,就會發現,這其實和藝術品的物質屬性有關。視覺藝術需要一種物質載體,在高度商品化的社會,只要一個事物具有某種物理形態,理論上講,就都可以明碼標價。

美國知名畫家洛里·伍德沃德曾經總結出為藝術品定價的簡單公式:將畫的寬度乘以長度,得出總尺寸,以此為單位,乘以符合畫家聲譽的固定金額。然后計算出畫布和畫框的成本,并在此基礎上翻倍。最后將兩者相加,就得出了畫作的市場售價。
上述公式之所以能夠成立,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理形態基礎上。當我們說某件藝術品很廉價時,首先指它的市場價格,也就是交換價值很低。但對于不同的人來說,它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使用價值,換句話說:其所能夠滿足某人需求的程度和方式是因人而異的。
因此,廉價的藝術可以僅僅就字面意思來理解,即它具有低廉的市場售價。那些便宜的作品,自然可以被認為是廉價的藝術品。但另一方面,這件作品可能對你來說很重要,很“值錢”。但這只是象征意義的表述而已。
藝術品只有以客觀標準為基礎,才能夠進行定價。就像著名藝術咨詢機構ArtBusiness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無論你的藝術有多么獨特,它在某些方面總是與其他藝術品有相似之處,比如尺寸、形狀、媒介、重量、主題、顏色和制作時間等等。
以此為依據進行定價,被形容為是“量化創造力”。

獨特性不是定價藝術的唯一標準
現在的問題是,當我們談論完全抽象的藝術——音樂時,以上這套理解方式和衡量體系就不再適用了。
沒人能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定價,能夠做到的,不過是把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手稿拿去拍賣,這里有一個關鍵區別:只有當某首音樂作品以一種物質形態的方式呈現時,它才具備交換價值。問題是,這些物質形態其實并不是音樂本身!
當我們聆聽音樂時,我們在肆意享受它的使用價值,但這種使用價值是無法轉化為交換價值的,無法通過某種市場價格體系予以標定。
當然,你也可以說,由于《第九交響曲》的手稿拍賣價格非常高(早在2003年,該作的總譜原稿便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被一位私人收藏家以213萬英鎊的高價競得),那么,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這首音樂本身很“貴”。但這種類比同樣只是象征意義的表述而已。
由于缺少一套準確、直接的轉化系統,音樂的價值便無法直接通過價格來展現。這就給如何評判音樂的藝術價值造成了困難。當缺乏一套客觀有效的衡量標準,我們就沒有足夠的底氣來為音樂“定價”了。

我們說某件藝術品很廉價,雖然首先指的是它的交換價值,但通常也包含了對其使用價值的評定。這兩者在多數情況下是緊密相關的,或者說,前者可以直接影響后者。當然,有時候決定其市場價格的因素與一些附加屬性有關,比如畫面相同的一幅油畫復制品,不同的裝幀工藝和印刷品質,會造成巨大的價格落差。
拋開這類情況不談,僅就繪畫本身而言,藝術品通過市場價格而呈現出的交換價值,通常也代表人們對其藝術水準的判定,從而體現了其使用價值的高低。
市場價格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抹平了每件藝術品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有時會成為使用價值的來源。問題是,正如ArtBusiness指出的那樣:“所有藝術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位藝術家都是獨一無二的。然而,獨特性不是,而且永遠不會成為定價藝術的唯一標準。”
一個看似冷酷的事實是:在藝術品被“真正出售之前,沒有任何東西是值得的”。
但對于音樂來說,除了類似于繪畫中的裝幀工藝這類因素尚且符合客觀的價格標準,音樂本身根本無法用客觀的價格體系來衡量。

價格從不體現音樂本身的價值
我們都知道音樂是一門藝術,但沒有誰會將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稱為藝術品,這一領域自然也不存在所謂的藝術品市場。
很多人也許會問:正版音樂的售價、實體專輯的定價,以及音樂會的門票價格,難道不都體現了音樂的交換價值嗎?事實上,它們要么體現的是版權價值,要么體現的是音樂家的價值,或者其它層面的附帶價值,而不是音樂本身的價值。
實體專輯的價格,很大程度上與唱片公司的錄音技術、唱片的材質工藝,以及版本的稀缺性有關。約翰·列儂與妻子小野洋子在1980年合作推出的《DoubleFantasy》這張專輯,曾經以52.5萬美元的起拍價拍賣,成為史上最昂貴的黑膠唱片。
如此高昂的價格并非因為音樂本身,而是源于約翰·列儂在這張專輯推出后不久便遭到槍殺身亡,《DoubleFantasy》因此成為了這位傳奇人物的天鵝之歌,上面印有他本人最后的簽名。而在這張拍賣唱片的封面上,還留有警方的物證編號、用黑色簽字筆寫下的“WJT-2”。
因此,也只有這一張《DoubleFantasy》才能夠賣出如此天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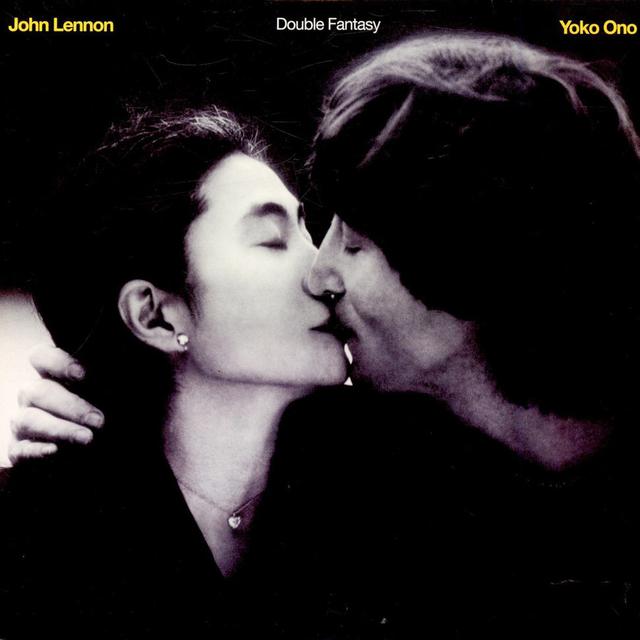
《DoubleFantasy》專輯封面
而在流媒體時代,音樂曲目通常擁有相對統一的網絡售價,顯然,價格在這里體現的是版權價值,而非每一首音樂作品自身的價值。
至于柏林愛樂演奏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和某不知名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賣出的門票價格可能相差數十倍。這只是因為柏林愛樂的身價更貴,和他們演奏的音樂本身無關。
并且,決定演出票價的因素有很多。2005年,西蒙·拉特爾攜柏林愛樂首次到上海演出,當時的最高票價賣到了4000元一張;而到了2017年,當拉特爾再度攜柏林愛樂到訪上海時,票價整整降了三分之一。
但這并不意味著柏林愛樂在這12年里的水準降低了,也不意味著第二次演出的作品價值不如首次到訪時演出的曲目。在不同情況下,演出團體的市場價格可能是浮動的,但這與音樂本身的價值毫無關系。
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在《音樂社會學》中從商品的角度來分析樂器。毫無疑問,樂器是音樂周邊最具量化特征的物質形態之一,但當一位小提琴演奏家用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昂貴名琴來演奏一首名不見經傳的小提琴協奏曲,并不會提升這首曲子本身的價值。

西蒙·拉特爾與柏林愛樂
如何為一首音樂“定價”?
音樂是真正無價的藝術。這種無價,不是建立在市場價格體系基礎上的“無價”,而是無法放在任何一種商業邏輯和市場經濟中去衡量。
但我們有時候的確會聲稱某些音樂作品是“廉價”的。廉價,成為了一個純粹象征性的詞語,在類比的意義上被理解。不過,當它被用來形容音樂時,尤其容易滋生一種觀念,即:在古典音樂愛好者眼里,所有流行音樂都是“廉價”的;或者在重金屬愛好者眼里,所有校園民謠都是“廉價”的。
盡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品位,很多時候,你很難真正說服一個與你趣味不同的人,但不能否認的是,藝術本身的確有高低之分。
但需要注意,即便是在古典音樂中,也有大量“廉價”的作品,它們的藝術價值甚至無法和一首經典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論。正如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音樂美學家周海宏指出的那樣:音樂作品藝術質量的好與壞,不是所謂高雅音樂與通俗音樂之間的本質差異。
因此,真正的古典音樂愛好者,決不會輕視一切流行音樂作品。并且,當我們用“廉價”來形容音樂時,不應用它來指代任何一種成熟的類型或風格,即便這種音樂是你根本無法接受甚至嗤之以鼻的。

情歌愛好者大可抱怨說搖滾樂太刺耳,但不能說所有搖滾樂都很“廉價”;同樣,搖滾樂愛好者可以說情歌顯得很矯情,但不能說情歌這個類型很“廉價”。
原因是,當“廉價”這個詞脫離了客觀的市場價格體系,在完全修辭的意義上使用和理解時,其強烈的情感傾向將變得無以復加。它所包含的情緒化與價值判斷,很容易熾烈到一種非理性的程度,以至于使人喪失了對事物的基本判斷。因此,對這個詞的使用,才應當非常謹慎。
實際上,要給一首音樂“標價”,即便只是在修辭意義上,也是很困難的事情。只有具備足夠的鑒別能力時,才能用這個難以駕馭的術語去形容一首音樂。而對于普通人來說,將個人喜好變成價值判斷的坐標,無疑是非常危險的。
周海宏指出,音樂普及的最基礎性工作,“在于培養人們聽覺感受的能力,與體驗內心精神世界活動變化的審美方式”。不同的音樂類型有屬于自己的審美特點,某些音樂可能不符合你的聽覺習慣,或者內心世界的審美喜好,但不代表它們就毫無價值。

享受“廉價”的藝術
面對音樂,我們應當保持愛我所愛的心態,對自己不喜歡甚至厭惡的風格或類型,保持足夠的距離即可。至于它們是否“廉價”,其實并不十分重要。
況且,任何一個時代,都充斥著大量“廉價”的音樂,對于當時的民眾來說,自有其存在價值,能夠滿足人們的現實需求。某些“廉價”的音樂作品,有朝一日甚至會變得“高貴”起來。
眾所周知,施特勞斯家族創作的大量圓舞曲,不過是貴族沙龍的助興音樂罷了。對于當時的音樂鑒賞家來說,其實顯得很“廉價”。但當它們出現在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上時,卻讓今天的觀眾感受到一種高級感。
就此而言,“廉價”也許并不總是一個貶義詞。許多時候,我們需要“廉價”的音樂來填充疲憊的身心;在碎片化的世界里,“廉價”的音樂似乎也更匹配我們的生活情境。
許多年前,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過背景音樂的大行其道:“看看我們自己,有誰敢宣誓,從沒有在喇叭里放著輕盈的音樂聲,同時卻在讀書、閑聊、做家務?”每當這種時候,我們其實什么也沒聽到,“只是感到一種愜意的聲浪像一層暖洋洋的絲絨毯裹在自己周圍,僅此而已。”

法國作曲家薩蒂早在19世紀便提出過著名的家具音樂理論,他認為這種音樂將被用來“填補有時在朋友之間一起用餐時的沉寂”,并“消除街道上的喧囂”。今天,專門的背景音樂承擔起了這一功能。許多情況下,我們只是在漫不經心地聽音樂而已。
即便像楊燕迪這樣的音樂學者也承認:“把音樂當作生活的背景和裝飾”,“仍不失為聽樂的一種方式”。
如果用平常心來接納這類“廉價”的音樂或者其他藝術,它們反而會豐富我們的生活。久而久之,“廉價”這個詞,也就不會帶有如此強烈的情感色彩,進而成為污名化的工具和狹隘觀念的口頭禪了。
當然,我們在消費“廉價”音樂的同時,不能忽視這個世界上還有更高級、更“昂貴”的音樂,它們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神去理解和欣賞,甚至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才能體會到高級事物帶來的巨大快感——一種從廉價事物中永遠無法獲得的滿足感。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不一味排斥,也不一味沉迷,或許才是對待“廉價”藝術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