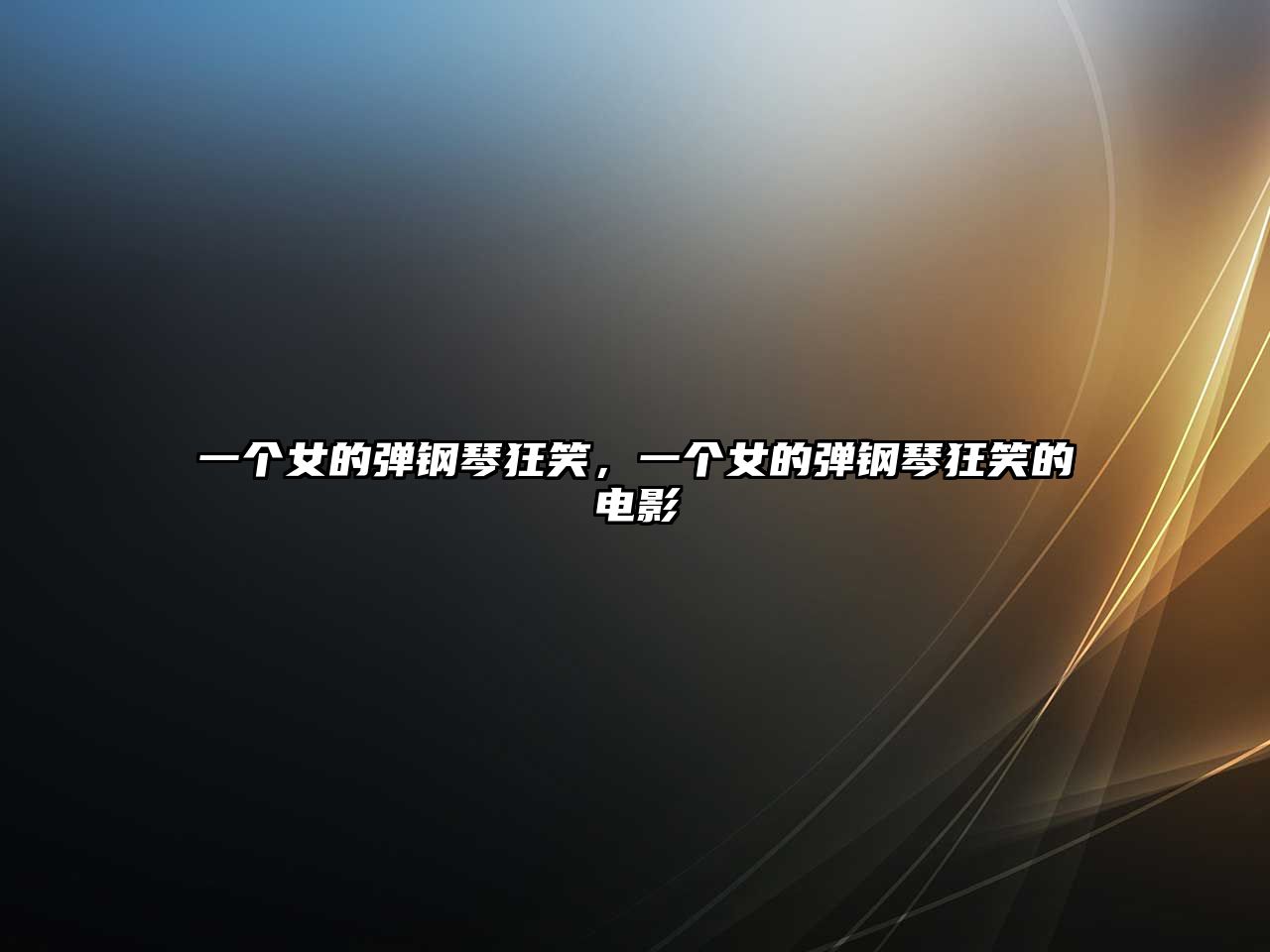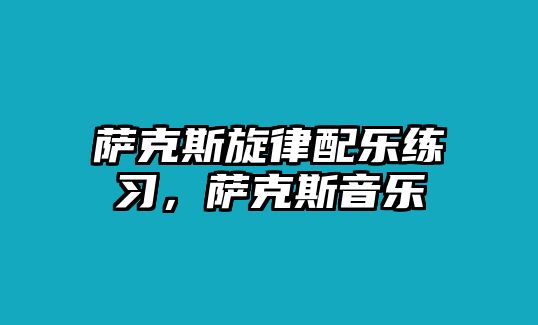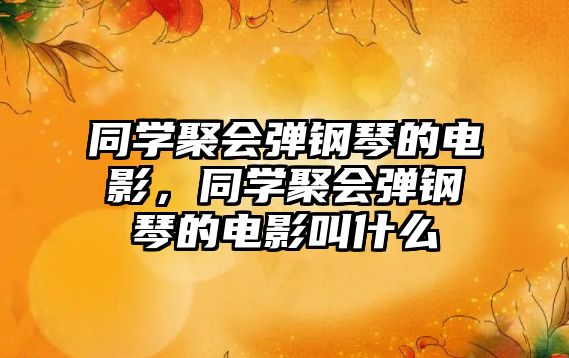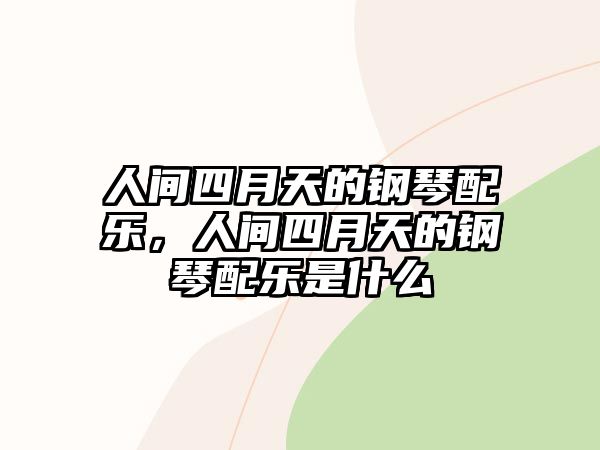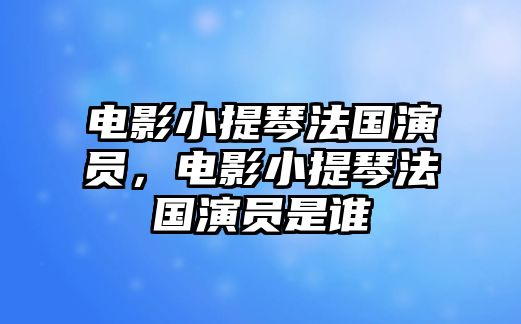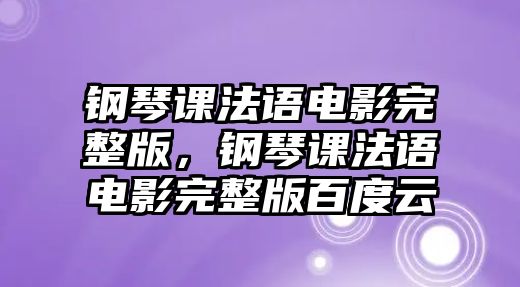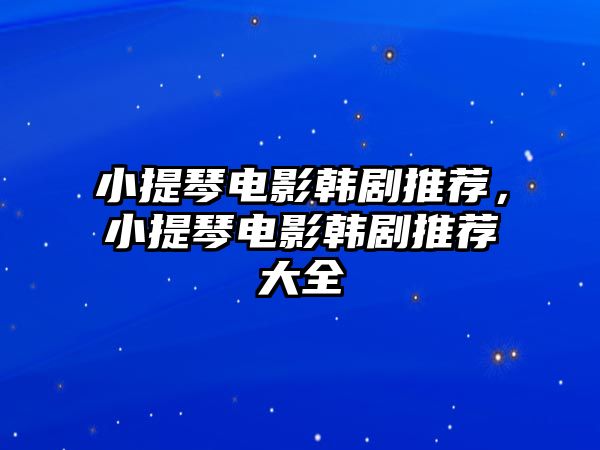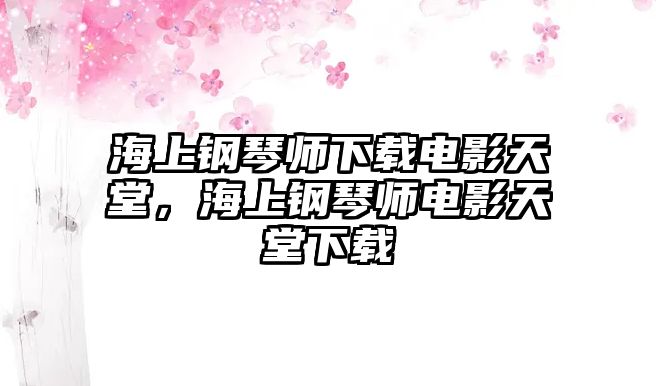僵尸之歌小提琴(一整個震撼盤點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電影配樂)
姜文說:“對,你就比莫扎特好一點就行了。”
聽完這話,久石讓石化了一個月才開始下筆,來來回回折騰了好幾個版本,姜文都不滿意,堅持用莫扎特的標準折磨久石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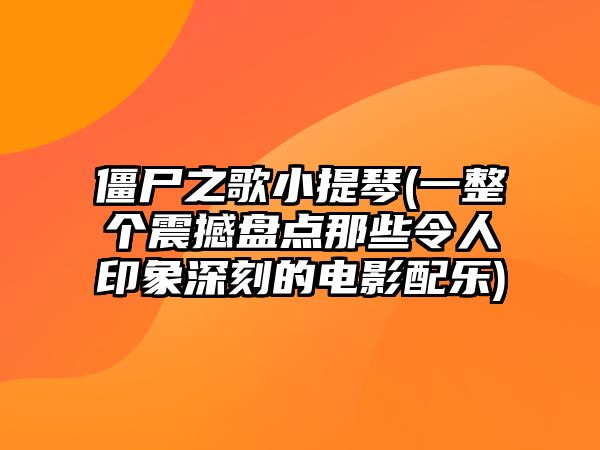
萬幸結果是好的,久石讓最后交出了一份讓導演滿意的答案,姜文甚至在采訪中不無得意地說:“如果莫扎特同志活著,說不定我也可以折磨折磨他。”
久石讓《太陽照常升起》
姜文太喜歡《太陽照常升起》的配樂,以至于在《讓子彈飛》開頭,再次使用了那首配樂。
另一個姜文重視配樂的例子,還體現在“民國三部曲”(《讓子彈飛》《一步之遙》《邪不壓正》)里。
如果仔細看這三部電影的片尾字幕就會發現,姜文沒有像其他商業電影那樣,以音樂作品為單位做介紹,而是采用樂器和演奏人的關系來介紹。
《驚魂記》主題樂《Prelude》
這首曲子用弦樂究極拉扯,提高它們鳴和速度的同時,拉低彼此的聲場,間或輔以小提琴刺耳的鳴奏,迅速把人代入到瓢潑大雨的夜晚,主角趁著昏暗車燈瘋狂逃命的情境里。
所以在接受采訪時,希區柯克說《驚魂記》33%的驚悚效果都來自配樂,還主動提出說要給赫爾曼加錢。
它最早出現在林正英的靈幻喜劇里,所以整體曲風稍帶跳脫,節奏也相對歡快輕松。
但當麥浚龍把它放在陰森恐怖的《僵尸》里做主題曲時,改編的效果就十分沉郁、哀婉,森冷中透著凄涼和怨憤。
可反觀坂本龍一為自己打造的專輯,比如評價極高的《async》。
整張專輯14首樂曲,從頭到尾聽下來,幾乎沒有旋律,而是由踩在落葉上的腳步聲、被海嘯損壞的鋼琴發出的聲音、測量核污染儀器的哀嚎聲、日本傳統的三味線等等聲音,奇妙地組合著。
與其說是在聽音樂,不如說是在聽聲音。
坂本龍一后期的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如此。
這也是為什么在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里,他可以給自己套個藍色塑料桶,站在雨中感受雨滴敲擊的聲音;可以深入叢林,收集踩在枯葉上的腳步聲;還可以去非洲記錄原始部落的歌聲,在肯尼亞的湖泊上采集大自然的聲音。
莫里康內把口哨、排笛、鞭子、打鐵的鐵鉆和加了弱音器的小號,一股腦地塞進這首配樂里,制造出一股粗糲、荒蠻又玩世不恭的無賴氣氛,與萊昂內那讓人血脈賁張的電影畫面相得益彰。
這次合作,讓這兩位小學同學互相成就了對方。
在這之后,倆人多次合作,包括“鏢客三部曲”、《革命往事》、《西部往事》和《美國往事》等。
《美國往事》主題樂
在萊昂內后期的電影里,莫里康內的音樂顯然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因為導演總是讓事先寫好配樂,然后在片場用高音喇叭放給演員聽,讓他們從莫里康內的音樂中找感覺。
這些電影明星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不同的語言,無法在拍攝中用臺詞直接對白。
于是莫里康內的音樂成了攝影過程中一種重要的無字臺詞——它催促著英雄和土匪們,披掛上場,血濺黃沙。
還有那首出現在《無恥混蛋》片頭的《TheVerdict[DopolaCondanna]》(大捕殺),莫里康內聽到后都很詫異:他(昆汀)是在哪翻出來的這首曲子?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在借用那么多年后,昆汀終于邀請莫里康內為《八惡人》做原創配樂。
2016年,昆汀親自帶著《八惡人》的意大利語版本飛往意大利,在錄音現場聽莫里康內帶人為電影配樂。
當莫里康內憑借《八惡人》斬獲奧斯卡時,負責頒獎的昆汀說了這樣一段話:“你們知道莫里康內是我最愛的作曲家吧?這里說的作曲家,可不是那些低檔的電影作曲家,我是指莫扎特、還有貝多芬、還有舒伯特——是這些大師們!”
<
下一篇
小提琴牧歌賞析,小提琴牧歌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