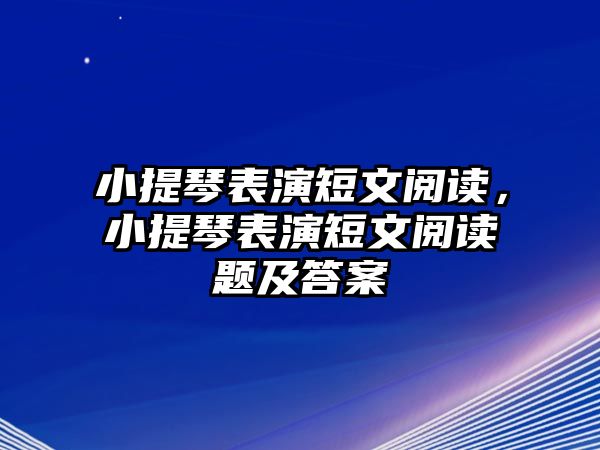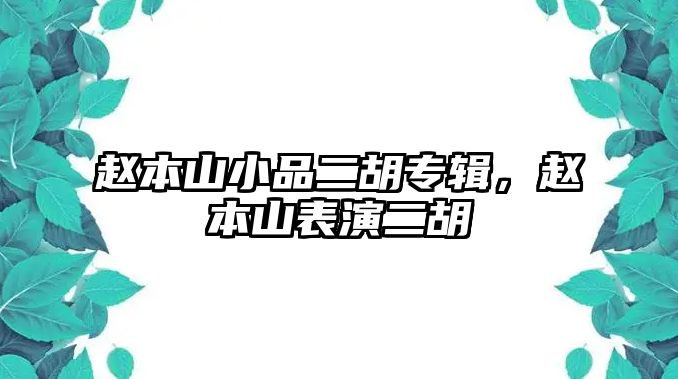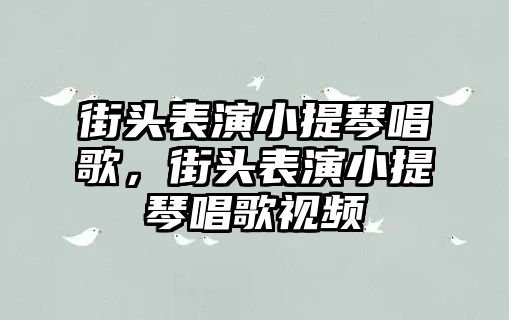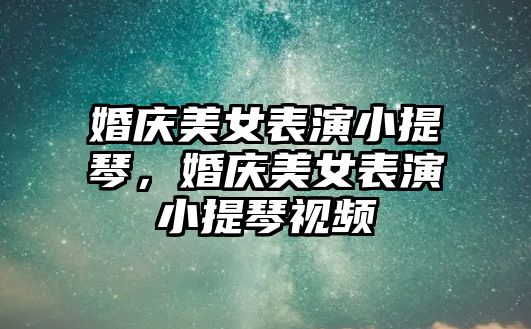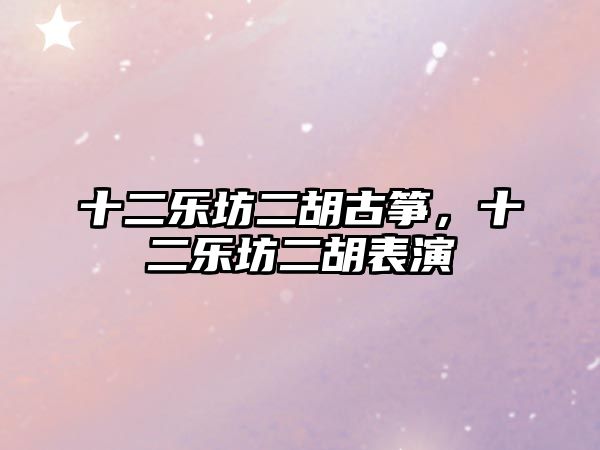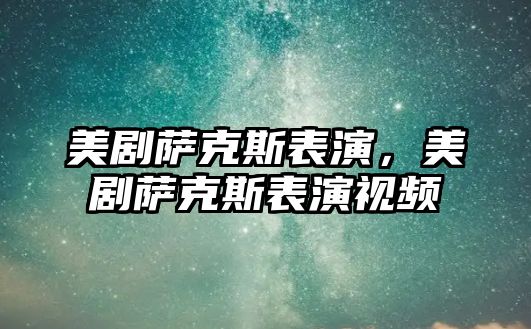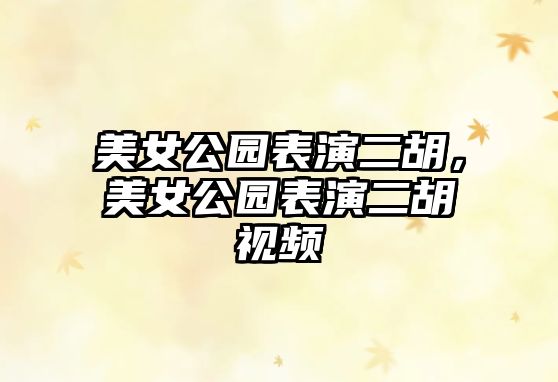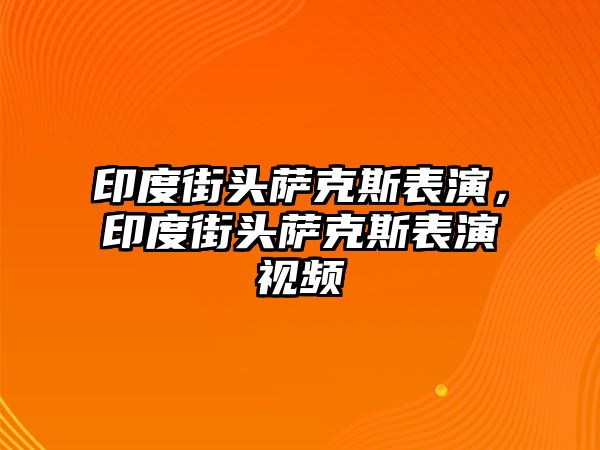喪事專用曲薩克斯(農村的“響器”)
在很多農村,誰家有了紅白喜事,都要請“響器隊”。“響器”是鄉村的人們對嗩吶、二胡、笙、鑼、鐃、鈸等樂器的籠統稱呼。不過,這個純粹的民族樂器隊伍里,現在也加入了很多西方元素,如電子琴、爵士鼓、薩克斯等。在我的家鄉,只有白事才請“響器隊”。
響器隊的表演分為整響和半響。整響與半響并不是說樂器有多大差別,而是表演的時間安排不一樣。整響從白事的頭天晚上開始,一直表演到午夜,白事當天照演不誤;而半響就是只在白事當天表演。可別看這個小小的差別,請整響的價錢一般是半響的兩倍以上,因為整響的表演人數要比半響多出好幾個,節目也更精彩。最精彩的,就是請兩班整響對著表演,但價錢還要高出一截兒。

響器隊一般由五到六人組成(整響往往超過十人),一人吹嗩吶,兩人吹笙,一人敲梆子或拍鐃鈸,一名女演員負責演唱戲曲選段,一名二胡手在演唱戲曲時負責伴奏。嗩吶手是整個響器隊的靈魂人物,也是最忙碌的:他左手拿著嗩吶,右手小指上掛著鑼槌,面前的桌子上還平放著一副小鐃。他時而吹奏,時而敲鑼,時而拍鐃,忙得不亦樂乎。于是衍生出一句跟大忙人開玩笑的話來,“比吹響器還忙啊!”
響器隊的表演場地過去很簡單,只是在平地上放兩張桌子、幾條長凳。現在則有了專門的舞臺,搭建在事主門前的大街上,高高的,跟小戲臺子一般。如果請兩班響器隊表演,就對著面搭建兩座舞臺,觀眾聚在兩座舞臺之間,可以左右逢源,便于觀看花樣迭出、精彩不斷的“對臺戲”。

響器隊的表演有兩次高潮,一次是晚間的表演;一次是中午宴席上的表演,叫做“吹席”。開始的時候,嗩吶手先吹奏幾曲凄婉哀傷的戲曲或現代歌曲,算是開場。接著,花樣嗩吶、戲曲、小品、魔術等吸引觀眾的節目才開始輪番登場。演到酣處,觀眾的喝彩聲和鼓掌聲連綿不斷,演員的勁頭兒一上來,即使寒冬臘月,也免不了赤膊上陣。遇到“對臺戲”,兩班響器隊一班比一班賣力,唯恐留不住觀眾。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自己表演得不好,下次是沒有人請的。更現實的是,表演最好的那一班,事主會在事前談好的費用外,多加上幾百元“獎金”。
在其它時間,響器隊則比較放松。每逢有人前來祭奠,執客就會大聲吆喝,“客到了,奠紙……”聲音拖得長長的,像唱戲一般。響器隊聽到執客的吆喝,才會“烏里哇啦”地應付著吹上一陣子,配合祭奠的氣氛。下午出殯的時候,嗩吶手左手腕上系著銅鑼,在兩個吹笙手的伴隨下,走在送殯隊伍的前面,一路上吹吹打打地送到墓地,也就完成任務了。
過去,鄉村文化生活比較匱乏,“聽響器”對于大家來說,絕對是一頓“大餐”,吸引得三里五村的人們紛紛加入到觀眾的行列。那陣勢,比起觀看專場的戲曲表演來,一點兒都不遜色。響器隊表演的勸人學孝、緬懷親人節目,也常常勾引得觀看的老老少少潸然淚下。
隨著時代的發展,響器隊表演的節目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異化現象:曲目不加選擇,什么流行演奏什么,有時候跟白事的哀傷根本沾不上邊。更有甚者,為了爭奪觀眾的眼球,在兩班響器隊演“對臺戲”時,找來女演員表演“****舞”,進行惡性競爭,傷了社會風化。這時候,上了年紀的老人就會搖頭連連嘆息:“不孝啊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