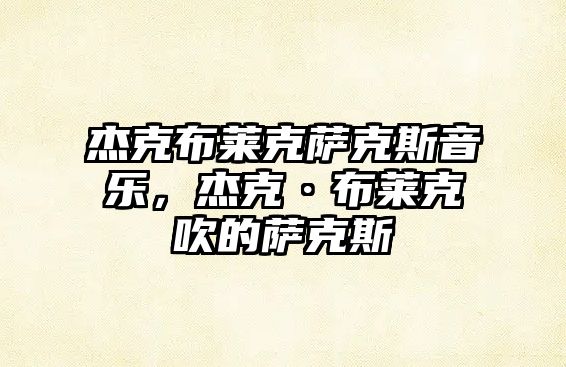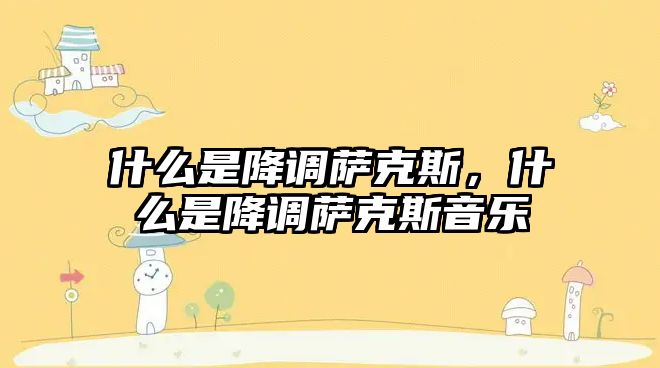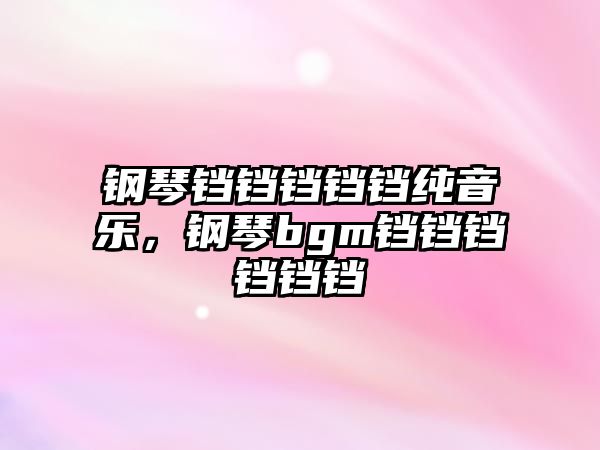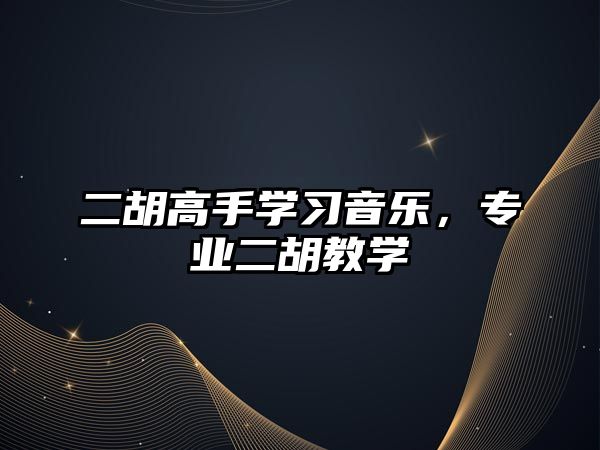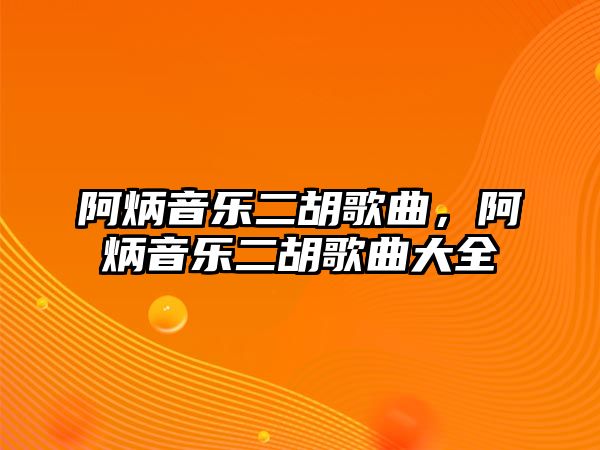白蛇傳經(jīng)典唱段薩克斯(《白蛇傳·情》畫(huà)風(fēng)令人驚艷之外,更有這些粵劇之美值得被看到)
-
 樂(lè)器資訊網(wǎng)
樂(lè)器資訊網(wǎng)
- 薩克斯
-
 2024-07-12 18:45:49
2024-07-12 18:45:49 - 瀏覽量:739

這些天,4K全景聲粵劇電影《白蛇傳·情》意外引發(fā)觀眾“自來(lái)水”推薦,并受到持續(xù)關(guān)注。截至目前,該片“豆瓣”評(píng)分為8.2分,“貓眼”觀眾評(píng)分為9.3分,均位居今年已上映影片之首。
“畫(huà)面唯美”“特效震撼人心”“傳統(tǒng)水墨風(fēng)好看”,觀眾趨向一致的評(píng)價(jià)背后,自然少不了片方的精心打造。將宋代繪畫(huà)的質(zhì)感融入電影畫(huà)面,既保留了傳統(tǒng)戲曲的精髓,也注入了東方美學(xué)意境;超過(guò)90%的鏡頭運(yùn)用特效,經(jīng)典橋段“水漫金山”的視覺(jué)效果更具沖擊力。
沉醉于《白蛇傳·情》的唯美震撼畫(huà)面,觀眾容易忘記此刻是在觀賞粵劇電影。然而,這對(duì)于粵劇本身而言,卻其實(shí)多少是一種遺憾。還有更多的粵劇之美、傳統(tǒng)戲曲之門(mén)道,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影片音樂(lè)動(dòng)聽(tīng)vs粵劇聲腔多元
“我覺(jué)得這電影中配樂(lè)和唱腔很好聽(tīng),不同于想象中戲曲。”
這是許多通過(guò)觀影而首次了解戲曲以及粵劇的觀眾的心聲。對(duì)于音樂(lè),片方毫不掩飾他們對(duì)于年輕人的“討好”,坦言“有別于傳統(tǒng)粵劇唱腔,不但更通俗流行,還融合了西洋管弦樂(lè),讓年輕觀眾更易接受。”可能是考慮目標(biāo)觀眾接受度以及經(jīng)費(fèi)投入與片長(zhǎng)控制等問(wèn)題,《白蛇傳·情》電影版與舞臺(tái)版相比,刪去了不少唱段,并有意減少“梆黃”味較重的部分。因此,有粵劇迷發(fā)表觀后感時(shí)表示遺憾,認(rèn)為該片“戲味”不足、部分唱詞過(guò)白。

其實(shí),粵劇聲腔由三種不同音樂(lè)結(jié)構(gòu)的曲調(diào)組成,主要是板腔體的梆子和二黃,其次是曲牌體的昆腔、弋陽(yáng)腔的曲牌和小曲以及說(shuō)唱體的木魚(yú)、南音、板眼等。不過(guò),這并非粵劇唱腔的完整面貌,據(jù)孔慶夫、金姚考證,粵劇唱腔曲牌來(lái)源多元化,“不僅有傳承自傳統(tǒng)文人、民間、宗教和宮廷音樂(lè)的唱腔曲牌,而且其通過(guò)對(duì)非粵地傳統(tǒng)器樂(lè)音樂(lè)的“移植”;對(duì)粵地器樂(lè)音樂(lè)的“變體”;對(duì)外江戲音樂(lè)、粵地說(shuō)唱音樂(lè)以及異質(zhì)音樂(lè)(電影音樂(lè)、流行歌曲、歐美音樂(lè)、海外戲劇音樂(lè)等)的“吸收”;以及對(duì)粵劇先賢音樂(lè)創(chuàng)作、音樂(lè)作品“堅(jiān)守”等途徑,大量發(fā)展了粵劇唱腔的曲牌結(jié)構(gòu)和數(shù)量。”此外,因受外來(lái)文化的影響,粵劇的音樂(lè)配器從八種發(fā)展至四十余種,約在百年前已開(kāi)始使用小提琴、大提琴、薩克斯管等西方樂(lè)器。

由此可見(jiàn),粵劇的聲腔與音樂(lè)在其形成與發(fā)展過(guò)程中表現(xiàn)出鮮明的包容性與靈活性,歷代粵劇藝人均有參與藝術(shù)改革。當(dāng)然,對(duì)于如何處理繼承傳統(tǒng)與吸納創(chuàng)新的問(wèn)題,應(yīng)該把握好尺度與分寸,否則就陷入舍本求末之境地。

粵語(yǔ)晦澀難懂vs唱念語(yǔ)言轉(zhuǎn)變
“粵語(yǔ)好難懂,為什么粵劇不能用普通話來(lái)唱。”
回顧粵劇的發(fā)展史,用北方方言唱粵劇還真不是“玩笑話”。粵劇的雛形是明代本地酬神土戲,明中葉以后陸續(xù)受到“外江班”的弋陽(yáng)腔、昆山腔、“梆黃”等影響。清咸豐、道光年間,廣東本地班的唱念語(yǔ)言,最初主要采用“戲棚官話”(以湖廣音中州韻為主),約至20世紀(jì)20年代才完全使用粵語(yǔ)演唱。粵語(yǔ)的聲韻系統(tǒng)促使粵劇唱腔在發(fā)聲和行腔上發(fā)生重大變化,比如小生及小武行當(dāng)采用“平喉”(真聲)替代“假嗓”(假聲)進(jìn)行演唱。

雖然如此,但時(shí)至今日仍能在粵劇中聽(tīng)到少許的官話詞匯。比如《白蛇傳·情》中“盜仙草”橋段,仙童見(jiàn)白素貞趕來(lái),喝道:“好膽,好膽!何方妖孽,竟敢闖我仙山”,此處“好”念作[haau3](音近粵語(yǔ)“孝”字),而非粵語(yǔ)中常用讀音[hou2](音同普通話“猴”字)。另外,還有法海的口頭禪“阿彌陀佛”中的“佛”。

作為世界“非遺”項(xiàng)目的粵劇,其特色之一就在于粵語(yǔ)本身。目前標(biāo)準(zhǔn)粵語(yǔ)有九聲六調(diào),保留了大量古漢語(yǔ)元素與義項(xiàng),兼之其中古音調(diào)多,且韻尾保留較好,比較接近唐詩(shī)宋詞的平仄格律。而粵劇唱腔,十分講究出字、歸韻、收聲,用粵語(yǔ)唱念尤為抑揚(yáng)頓挫,婉轉(zhuǎn)動(dòng)聽(tīng)。

女主武藝高超vs武旦“出手”不凡
“當(dāng)我看到盜取仙草、勇闖佛寺和水漫金山,我感覺(jué)白素貞和小青變身武藝高超的女俠。”
在影片中,武打場(chǎng)面集中在小青與白素貞闖入金山寺一段,小青揮舞雙劍與眾僧周旋,白素貞則以水袖為武器與棍僧大陣對(duì)決。導(dǎo)演意在“將傳統(tǒng)戲曲舞臺(tái)絕活和世界聞名的中國(guó)功夫有機(jī)結(jié)合,將東方美學(xué)與傳統(tǒng)文化的剛?cè)岵?jì)展現(xiàn)無(wú)遺”。此段處理得相當(dāng)成功,融合得不著痕跡,使得不少對(duì)戲曲了解甚少者以為這不過(guò)是在滿足劇情需要之下,將傳統(tǒng)武術(shù)加以特效化的呈現(xiàn)。

不同于電影版,《白蛇傳·情》舞臺(tái)版以戲曲專(zhuān)屬語(yǔ)匯演繹獨(dú)具魅力的武打場(chǎng)面。此橋段屬各劇種中常演的武戲之一,通常放在“水斗”一折,而且往往“出手”不凡,令人喝彩叫好。
“出手”是戲曲行話,表現(xiàn)女將力拒眾敵、英勇善戰(zhàn)或亂軍中搶奪兵器的情節(jié)。以打出手者(武旦為主)為中心,稱(chēng)“上把”;另有幾個(gè)拋扔武器者為“下把”,相互配合,作拋、擲、踢、接武器的特技表演。雙方在邊扔邊踢的同時(shí),還要不時(shí)變換舞臺(tái)調(diào)度,組成“斜一字”“五梅花”等各種排場(chǎng)。

此劇的“水斗”場(chǎng)面更為壯觀,既吸收借鑒京劇《白蛇傳》和昆曲《雷峰塔》的功架,又利用演員特長(zhǎng)而對(duì)表演程式進(jìn)行突破創(chuàng)新。白素貞一人對(duì)陣十二名金剛,雙腳前踢后趟拋來(lái)的花槍?zhuān)p手不使用傳統(tǒng)雙槍?zhuān)歉臑橥瑫r(shí)舞動(dòng)七尺水袖,以柔制剛,左推右擋,將單拋袖、平揚(yáng)袖、下抓袖、單云袖、雙上下?lián)u袖、雙直搖袖、轉(zhuǎn)身刀花袖、繞袖原地轉(zhuǎn)等動(dòng)作行云流水般貫串其中。而且長(zhǎng)水袖的使用具有多重作用,其一,就角色形象而言,能延伸表現(xiàn)白蛇蜿蜒運(yùn)動(dòng)的姿態(tài)以及受傷后的劇痛難忍;其二,作為道具而言,有助于人物塑造,傳達(dá)白素貞內(nèi)心情感,反映為情抗?fàn)幍挠⒂屡c無(wú)奈;其三,就表演效果而言,展示演員的過(guò)硬功底,增加身段表演的可觀性。凡是看過(guò)現(xiàn)場(chǎng)版的觀眾,無(wú)一不被曾小敏的精彩絕倫的表演所吸引折服。

實(shí)際上,粵劇與電影結(jié)緣已久,但過(guò)往者多是將戲曲置于實(shí)景中表演而已。而《白蛇傳·情》,盡管故事文本與人物塑造等方面存在不足,但能在電影與戲曲、寫(xiě)實(shí)與寫(xiě)意以及特效與程式之間,思索如何取舍與平衡并作出有益的嘗試,確實(shí)難能可貴。當(dāng)然,片方深知單憑一部電影不可能完成推廣粵劇的使命,因此影片并無(wú)刻意宣傳或普及粵劇知識(shí),即使在片尾亦未留下任何相關(guān)“彩蛋”。在重拾文化自信的時(shí)代,作為戲迷的我仍然期待這種“曲線”方式能喚醒更多人對(duì)于戲曲之美的認(rèn)知,有更多人愿意了解粵劇,觀賞粵劇,并成為知音。

作者:夕夜如風(fēng)(一位二刷《白蛇傳·情》的戲迷)
編輯:陳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