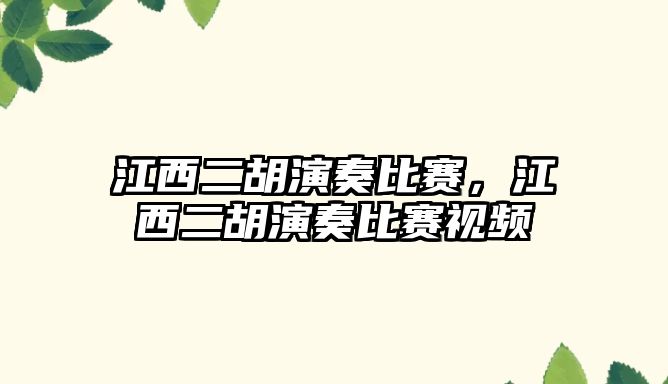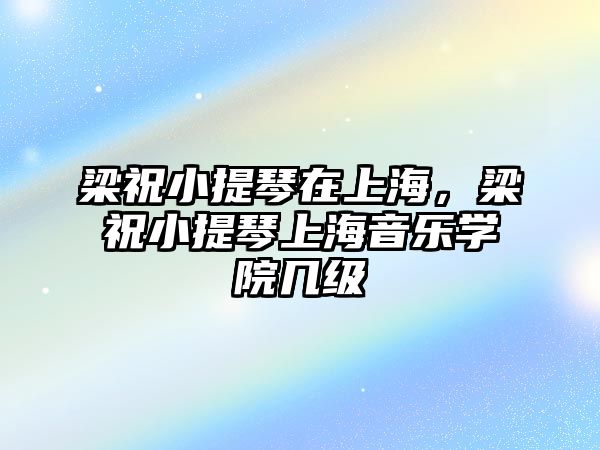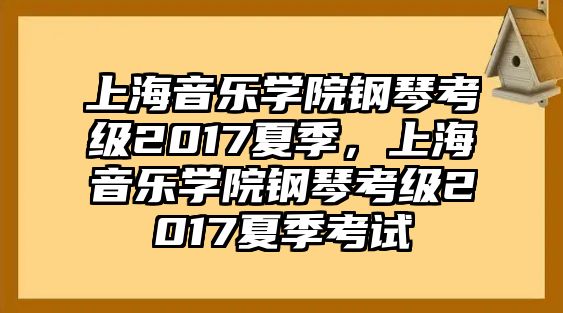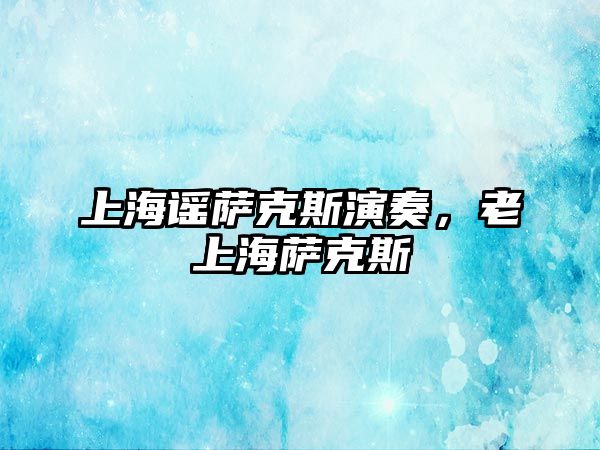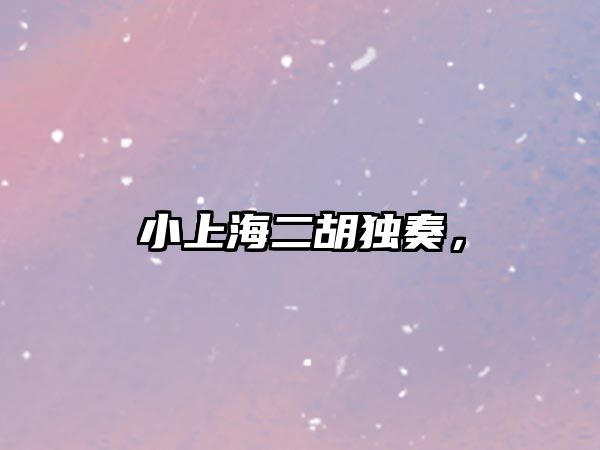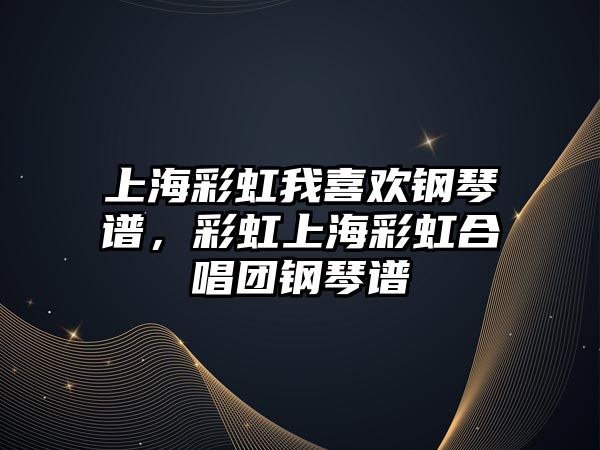我不能輸薩克斯(作別,上海最后一塊成片二級以下舊里的“蒼蠅館子”)
-
 樂器資訊網(wǎng)
樂器資訊網(wǎng)
- 薩克斯
-
 2024-07-04 14:28:46
2024-07-04 14:28:46 - 瀏覽量:920
上海最后一塊成片二級以下舊里
黃浦區(qū)建國東路67、68街坊
今天在二輪簽約中達到85%的生效比例
居民們就將告別蝸居
這一地塊沿著順昌路,云集著小吃店、炒貨鋪、美發(fā)廳等一批簡陋的鋪子,流動的是最鮮活的上海市井生活。我們走入順昌路上的網(wǎng)紅“蒼蠅館子”——江西飯店,以這個小小店鋪,留存下一段城市記憶的細枝末節(jié)。

“一條街誰不知道我兇悍,一說江西飯店那個女孩,能干,就是兇了點。其實我剛來上海的時候,跟人說一句話都會臉紅。”
李琴英,30出頭的江西姑娘,十幾歲時就跟著父母來到順昌路,在這個租來的30平米空間里開始上海的闖蕩。“要環(huán)境的不要來,要服務(wù)的不要來,要態(tài)度的更不要來!”憑借門口張貼的霸氣宣言和那煙熏火燎中誘人的濃香,李琴英的店在抖音、小紅書上火得讓她意外。對她來說,潑辣只是一種生存的保護色。
“我們以前被很多人坑,客人經(jīng)常逃單,喝了一點酒就吵架,我就是輸人不能輸氣勢,我看起來像一個打死一頭牛的人,我的青春沒有漂亮過,我一開始就為爸媽活了,就想爭口氣讓他們過得好一點,至少要在縣城里頭有一套房,我就是這個堅持下來的。”李琴英手里一邊理著菜,一邊回憶著,要強的她此刻的眼神中透著一絲憂傷。

開著超跑來的老板,戴著墨鏡的明星,穿著前衛(wèi)的網(wǎng)紅……這家最初只是被辛苦討生活的人們青睞的便宜小館子,很快有了更多元的擁躉,這讓李琴英錢包鼓起來的同時,也讓她感受到來自這座城市的認同感、歸屬感,使她慢慢變得柔軟起來。
“上海就是我的第二個家,在上海我錢也賺到了,我爸媽現(xiàn)在是全村第一富。我現(xiàn)在上海話全都聽得懂,也會講一些了,不管洋涇浜也好,主要是招呼那些爺叔、阿姨,我也能撒嬌,一個字‘嗲’,‘阿姨好,儂好哇啦,可以了哇’。”

每到入夜時分,江西飯店就會熱鬧起來,李琴英并不知道這些煎炒烹炸、家長里短的聲音,對住在樓上的上海房東來說有著一種莫名的安全感。
“晚上睡覺,感覺好像是安全感,現(xiàn)在沒吵聲我就不習(xí)慣,有溫暖的感覺。”江西飯店的房東王禮珊,68歲,單身一人照顧從小就腦癱的姐姐,14平米的房間和樓下租出去的空間是從父輩那里繼承來的。年輕時她曾自己在這里開過本幫菜館,也是當(dāng)時街上出了名能干的女老板,后來父母年邁,她才把店盤出去專心照顧家人。對于極少出遠門的她來說,順昌路幾乎承載了她生活的全部。
“有種自豪感,又能照顧姐姐,又能開飯店,感覺應(yīng)該做的事情都做了,對得起家里人,對得起父母交代我的事。”在王禮珊看來,日子雖然辛苦,可在順昌路與街坊們相伴走過的歲月,已讓她足夠滿足。

臨近搬遷前,喜歡獨處的王禮珊越發(fā)頻繁地到樓下的江西飯店看看。因為這熱氣騰騰的畫面,很快會成為記憶里永恒的片段。雖有感傷,但一輩子堅強的她早已為今后的日子做好打算。
“今后總歸帶著我姐姐去靠醫(yī)院近一點的中心區(qū),因為她越來越不行了,看病方便一點。一般我不流眼淚,如果說我姐姐她萬一走了,我會很難受,盡量就對她好一點。”王禮珊哽咽著說。
和王禮珊一樣,李琴英最近也開始抽出時間,用手機盡可能多記錄下順昌路最后的模樣,鏡頭里江西飯店那個大紅招牌總是閃閃發(fā)亮。“這條街都快拆完了,多拍點視頻保存好,記錄下這條我們喜歡又熟悉的老街,它就像自己老家一樣。我跟我老公說等我們七老八十了,打開來看一看。”

對于搬離,李琴英雖然不舍,卻絲毫不擔(dān)心未來,她和家人們已經(jīng)在打浦路盤下一個新店面,她很自信那將是一個“不會太差”的新起點。她篤定地說,“我們一家人,我的舅媽多能干,我的表弟、堂弟都超級能干,還有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我們有好手藝又都是勤勞的人,我們就可以再去把打浦路搞紅,對不對。”
說話間,樓上斷斷續(xù)續(xù)飄出一曲《送別》,那是房東王禮珊用薩克斯風(fēng)吹的。這些年,這個孤單而獨立的女人,迷上了這個和她有著一樣氣質(zhì)的樂器。每天薩克斯風(fēng)略帶憂傷的曲調(diào)會不時從這家江西飯店樓上傳出來,與順昌路各種小店的嘈雜聲交織在一起,碰撞著融合,就像這座城市里來來往往的人群和包容的文化一樣。

寫在后面的的話:
“最重要的事正是那些發(fā)生在街道上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江西飯店老板和上海房東在一幢逼仄空間里交錯發(fā)生的小事,是順昌路一天天、一年年上演的萬千故事中小小的存在,它們交匯在一起,構(gòu)成了上海最后一塊成片二級以下舊里最真實的模樣。
這模樣是碰撞的模樣。盡管狹小的居住空間相似,但上海的阿姨爺叔們?nèi)匀粫谏钪袑ふ仪檎{(diào),在街頭給自己的寵物狗整一個時髦的造型,去老盛興吃碗冷餛飩,或是打扮一番看戲看電影,而相比之下,那些租住在這里的外來客幾乎生活中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停地工作。

這模樣也是包容的模樣。在路面上切菜洗碗,在家門口擺一方小桌吃飯,在門鋪前玩著手機、說著閑話,家家戶戶都將日子鋪在了街面上,這種活動空間的局促反而加速了本地人和外來者之間的依賴和融合,于是就有了本幫菜里加點辣、江西菜里多點甜。本地房東年紀(jì)大了不方便做菜,外地房客做飯時就捎帶一份;外地街坊遇到辦事困難了,就找“更有見識”的本地鄰居商量。相比環(huán)境優(yōu)渥的社區(qū),這里的人們更加懂得彼此生活的不易,也更加知道相互包容、相互扶持的重要。
與江西飯店相隔100米左右的一家金陵湯包店再過一個月也將搬離,雖然不舍,但店主在這最后的日子里仍然斗志滿滿,熱情地招呼著每位客人,看到店里有人拿著隔壁本幫餐廳的綠豆湯外賣,就借過來認真地把包裝和價格研究一遍,她說之后她會回揚州老家開店,可以學(xué)著把這招帶回去,吸引客人。

作別順昌路后,每戶人家的最終去處各不相同,但在平凡的、瑣碎的,時常無奈的生活中,堅強地、溫暖地、向上地去生活,將是這條街留給曾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最珍貴的共同財富。
來源:上海新聞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