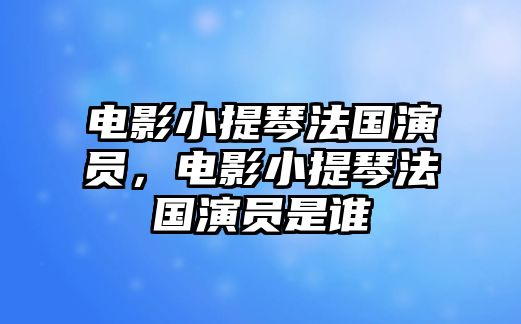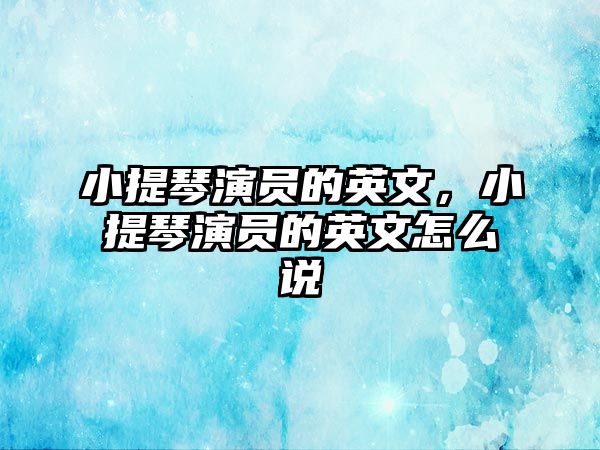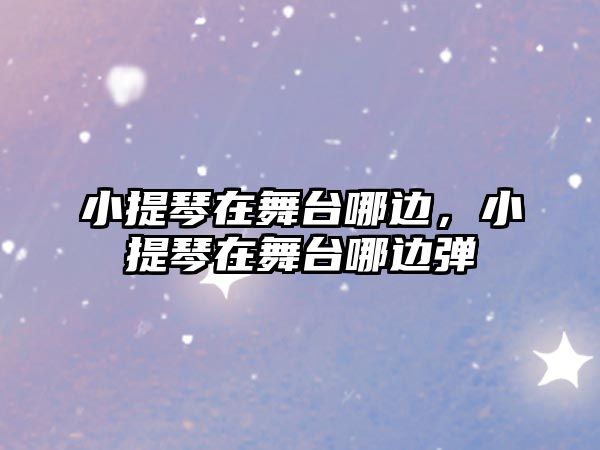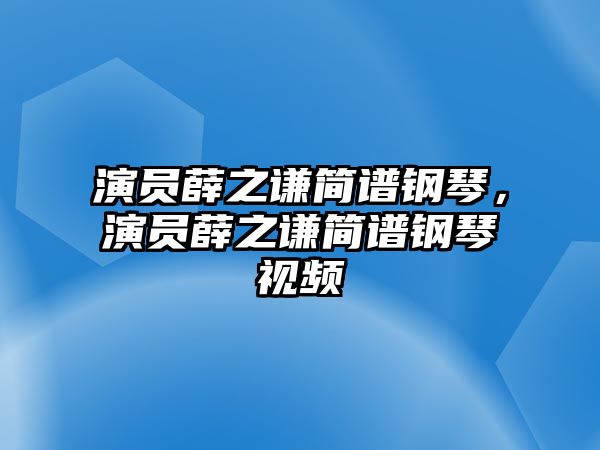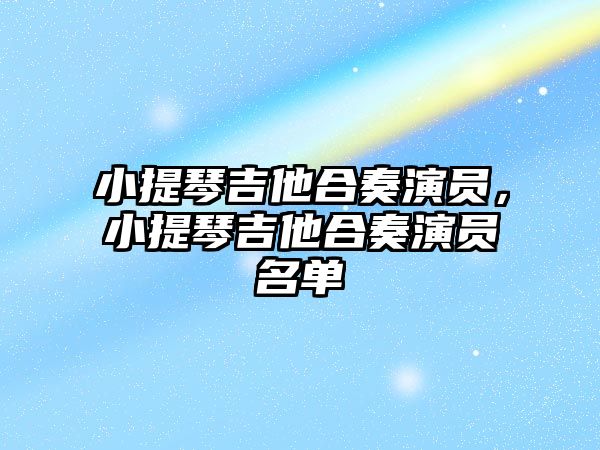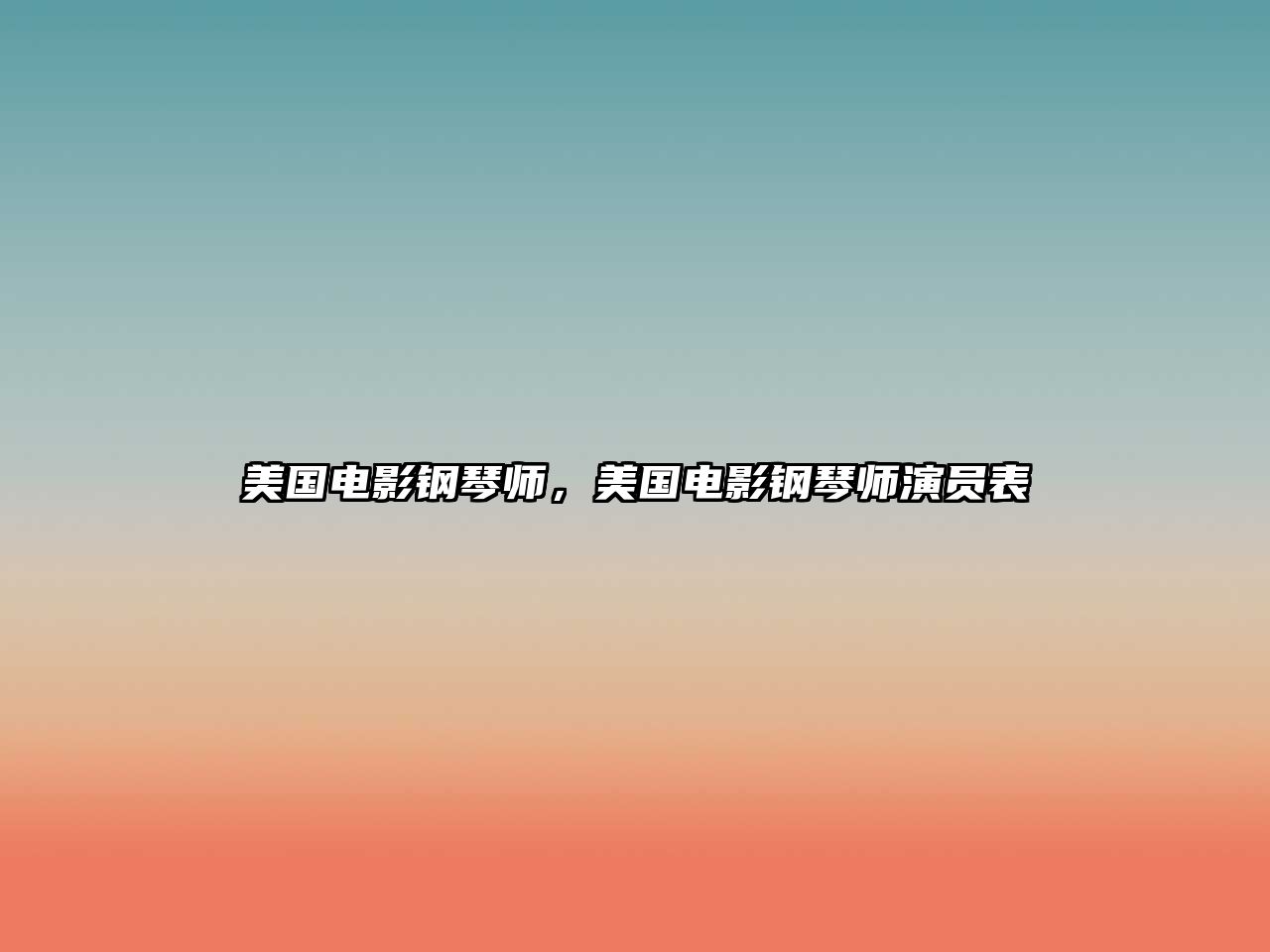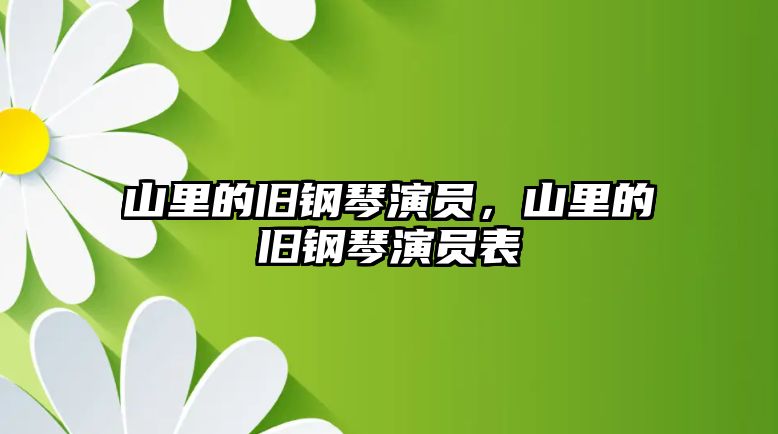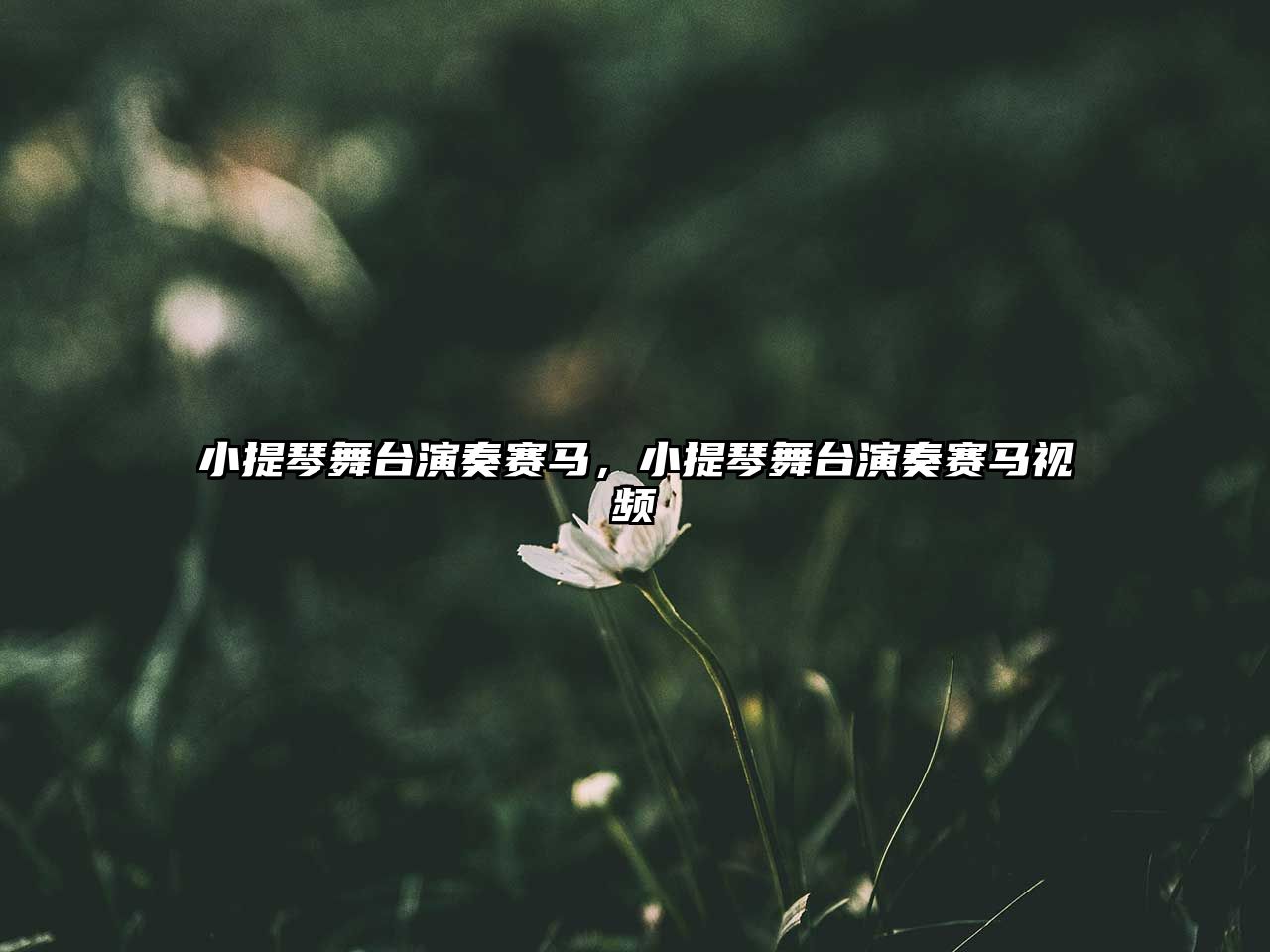伴奏粵劇薩克斯(洋樂器、西洋畫一度成粵劇“標(biāo)配”?藝術(shù)之路越走越返璞歸真)
-
 樂器資訊網(wǎng)
樂器資訊網(wǎng)
- 薩克斯
-
 2024-05-13 11:00:02
2024-05-13 11:00:02 - 瀏覽量:742
一桌二椅,卻生出無窮變幻,是公堂是宮殿也是山水;提琴吉他,也曾用進(jìn)粵劇音樂,粵劇的“洋氣”程度或讓你驚訝。說起粵劇,現(xiàn)在人們或仍能哼唱一二,卻很難說自己愛看粵劇、懂聽粵劇。粵劇之美是什么?服裝除了華美還要講究什么?粵劇的趣味在哪里?你可知臺(tái)上演員臺(tái)下樂師曾以手勢溝通?廣州日報(bào)推出“南國紅豆”下篇,面向普羅大眾尤其年輕人,介紹品味粵劇的門道。
○唱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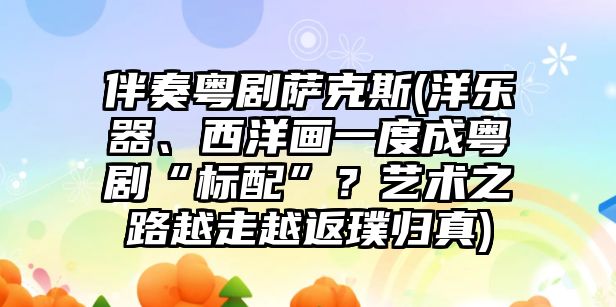
▎紅腔“柴房自嘆”博得滿堂彩
“我似寒梅遭暴雨,似寒梅遭暴雨,片片落階前”,同唱“寒梅”,前句如泣似訴,后句慷慨悲歌,一揚(yáng)一抑,句句誅心。
這是粵劇《搜書院》最著名的“柴房自嘆”唱段。今年3月7日,紅豆粵劇團(tuán)把此劇再次搬上中山紀(jì)念堂的舞臺(tái),由粵劇藝術(shù)大師紅線女的入室弟子蘇春梅演繹“翠蓮”一角。她的“柴房自嘆”盡得紅腔精髓,歌音清越,行腔婉轉(zhuǎn),唱出了翠蓮被困樊籠的哀怨與不甘、控訴與堅(jiān)強(qiáng)。憑借此劇中精彩的表現(xiàn),蘇春梅獲得了28屆中國戲劇梅花獎(jiǎng)。
很多人說,欣賞粵劇最重要得學(xué)會(huì)聽,多變的唱腔是粵劇相比其他傳統(tǒng)戲劇最大的特色。廣州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研究院戲劇部主任羅麗告訴記者,在粵劇的形成過程中,一路吸納了外來唱腔,并使之本土化。唱腔的兩大類是生角多用的真嗓和旦角多用的假嗓。“除了身段外,唱腔是展現(xiàn)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很重要的手段。”
粵劇中有多個(gè)流派唱腔,比如廣州人熟悉紅線女的“紅腔”、馬師曾的“馬腔”,還有“薛馬白廖桂”五大名腔。羅麗介紹,流派唱腔是指某一演員根據(jù)自己的嗓音條件、演唱習(xí)慣、“首本”劇目創(chuàng)造的一整套具有獨(dú)特風(fēng)格、適合自己演唱的唱腔。
▎檸檬小販啟發(fā)馬師曾創(chuàng)造“乞兒腔”
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故事莫過于馬師曾獨(dú)創(chuàng)“乞兒腔”。“我姓余,我哥老豆又系姓余……”這段500多字的“有序中板”,馬師曾唱來跌宕有致、揮灑自如,揭示了義乞余俠魂正直善良、好抱打不平、仗義助人的性格。特殊的唱腔令觀眾為之雀躍。
馬師曾深諳戲曲必須要通俗化、大眾化,讓聽眾聽得明白、聽得過癮的訣竅。在演出《苦鳳鶯憐》前,他就苦思冥想要?jiǎng)?chuàng)造適合余俠魂性格、氣質(zhì)的“乞兒腔”。有一天,他聽到賣檸檬的小販叫賣聲,覺得很有味道。他領(lǐng)悟到:小販叫賣的語言通俗易懂,聲音長短高低富于變化,讓男女老少都記得牢。他還吸納了大量廣州話、俚語入曲,創(chuàng)造出滑稽、跳躍、別具一格的“乞兒腔”。
▎蘇春梅三十年來每天跑圓臺(tái)練唱
這些獨(dú)特的唱腔在粵劇歷史上異彩紛呈、爭奇斗艷,獲得觀眾認(rèn)可并廣為傳播,也獲得了自己的“追隨者”。
蘇春梅便是深得紅線女真?zhèn)鞯摹白冯S者”。“一開始是逐字逐句地模仿紅老師的唱法,后來對(duì)翠蓮這個(gè)角色有了自己的理解,就開始創(chuàng)作,把前人藝術(shù)精華化為自己的東西。”演出后,蘇春梅在后臺(tái)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她還說,在粵劇中人物的情緒、性格也需要通過唱腔技巧表達(dá)。練習(xí)唱腔技巧只能多唱,熟能生巧,巧能成精。“從藝30年,我?guī)缀趺刻於荚诩遗芤粋€(gè)小時(shí)的圓臺(tái),一邊唱一邊跑,練抬腿功時(shí)也唱,練得喘氣時(shí)自然氣就沉在丹田了。演員不練功很容易退步,唱功也是。
○音樂
▎演員樂師用暗號(hào)交流“爆肚”演戲
粵劇音樂包含兩大部分,一是人聲的演唱,二便是器樂的伴奏了。在粵劇藝術(shù)博物館的音樂展區(qū),記者看到了兩件讓人驚訝的展品:一件是有近百年歷史、西德制造、用于粵劇伴奏的小提琴;另一樣是26個(gè)“手影”姿勢,演員在臺(tái)上通過手指或手掌作出的不同動(dòng)作暗示“棚面師父”(樂隊(duì)樂手)需要的鑼鼓或梆黃曲牌。
粵劇所用樂器,初期只有高胡、二弦、揚(yáng)琴、喉管、卜魚(板)、沙鼓、雙皮鼓、大鈸、文鑼、高邊鑼等民族樂器。20世紀(jì)20年代初30年代末,粵劇引進(jìn)了小提琴、薩克斯管(戲行稱“色士風(fēng)”)、吉他等西洋樂器,其中小提琴更被戲班引進(jìn)為“頭架”(即領(lǐng)奏樂器)。
由于西風(fēng)漸進(jìn),甚至有一段時(shí)間,粵劇臺(tái)上一件民族樂器也沒有。香港粵劇演員梁漢威曾分享一個(gè)故事:薛馬爭雄期間,雙方各出奇謀,馬師曾曾有一劇完全沒有鑼鼓,只用爵士樂。“找了一個(gè)人吹色士風(fēng),由頭吹到尾,結(jié)果是沒有人看這劇,慘敗了。他終于明白到鑼鼓對(duì)戲曲的重要性。”
但時(shí)至今天,粵劇音樂中仍有少量西洋樂器,比如《搜書院》的“棚面師父”中的一位就是大提琴手。香港粵劇演員阮兆輝表示,由于民族樂器中低音樂器不多,大提琴與大阮和革胡配合,為粵劇音樂的低音部分增添了色彩。
至于“手影”,在今天的粵劇舞臺(tái)上幾乎消失了。羅麗介紹,粵劇劇本最早的形態(tài)是“提綱戲”,沒有完整劇本、甚至上臺(tái)前沒經(jīng)過排練。演員和樂手上臺(tái)就能演能伴奏,靠的是默契和“手影”,而現(xiàn)在粵劇表演多是嚴(yán)謹(jǐn)?shù)匕凑談”尽?dǎo)演指導(dǎo)演繹。“在學(xué)者看來這有利有弊,其實(shí)即興、‘爆肚’也是粵劇很大的魅力。”
據(jù)阮兆輝回憶,馬師曾是一個(gè)讀了很多書、靈活而且有腦筋的人。在做戲方面他可謂完全掌握觀眾,連“棚面師父”也怕了他,要金睛火眼地看著他做戲。有時(shí)他會(huì)忽然“爆肚”,因?yàn)樗吹接^眾在臺(tái)下差點(diǎn)兒睡著了,便另起一段曲喚醒他們。
○衣箱
▎從主角到轎夫,戲服全為真絲面料
“存叔,我上臺(tái)第一件衫著邊件好啊?”在《搜書院》開場前,扮演書生張逸民的文武小生陳振江匆匆來到服裝部,向“衣箱叔父”袁存請教該穿湖水藍(lán)、還是紫藍(lán)的長衫。“紫藍(lán)沉穩(wěn)些,湖水藍(lán)青春些,湖水藍(lán)吧,后面的戲要穿更深的顏色。”存叔根據(jù)角色需要給出了答案,
粵劇戲班把置放戲服的木箱稱為“衣箱”,而保管戲服的部門崗位也用“衣箱”去命名,將管理戲服和負(fù)責(zé)幫演員穿著戲服的人員亦叫“衣箱伯父”或“衣箱叔父”。如今,“衣箱叔父”袁存也負(fù)責(zé)設(shè)計(jì)粵劇戲服。
袁存介紹道,由于粵劇演員在臺(tái)上會(huì)出很多汗,所以演員首先要穿一件全棉的、能吸水的水衣,以保護(hù)造價(jià)昂貴的漂亮戲服。在粵劇藝術(shù)博物館記者還看到一件“竹水衣”,由磨細(xì)的竹片抽絲編制而成,既涼快又能隔絕汗水。
戲服之所以昂貴,除了它上面精細(xì)的廣繡工藝,也與材料有關(guān)。袁存告訴記者,紅豆粵劇團(tuán)的戲服幾乎全部都是真絲,連轎夫也穿真絲。“因?yàn)檎娼z上舞臺(tái)‘吸光’,燈光打下去,不會(huì)反光。如果穿雪紡,現(xiàn)在看著很漂亮,上了舞臺(tái)燈光一打就會(huì)反光了。”而且真絲戲服即使穿很久,一上臺(tái)燈光一打效果跟新的一樣。“燈光和舞美是我們服裝設(shè)計(jì)的靈魂,必須要相互配合,服裝設(shè)計(jì)才會(huì)漂亮。”他說。
▎曾用珠筒裝、膠片裝甚至燈泡裝招徠觀眾
在粵劇藝術(shù)博物館的服裝展區(qū),有四件密密麻麻地釘著彩色珠片的戲服吸引了參觀者的眼光。在燈光的照耀下,珠片閃閃發(fā)亮,武生大靠的靠旗也閃耀著金光。
“珠片(也稱膠片)服裝一是為了突出演員,二是為了在昏暗的場合下比如在鄉(xiāng)間演出時(shí),用珠片反射光芒,讓舞臺(tái)效果更突出。”博物館講解員麥鏡波向記者介紹道。上世紀(jì)30年代,粵劇戲班競爭激烈,“華麗”“新奇”成了吸引觀眾的手段。藝人間爭妍斗麗,一度流行珠筒裝、膠片裝,把幾十斤重的金屬片釘在袍甲上創(chuàng)作“效果”。
在佛山的一個(gè)粵劇博物館里,有一件“燈泡裝”,除了釘繡著密密麻麻的珠片,還鑲上了很多電燈泡。麥鏡波說紅線女不喜歡這類戲服,因?yàn)樗紫群苤兀┥虾笱輪T施展不開,其次會(huì)搶光演員風(fēng)頭,觀眾將目光投注在戲服上,便會(huì)忽略演員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到了上世紀(jì)50年代,這些過于追求“華麗”的服飾漸漸在舞臺(tái)上消失。
關(guān)于粵劇戲服還有一個(gè)講究,就是“寧穿破,勿穿錯(cuò)”。粵劇一級(jí)演員、廣東粵劇院創(chuàng)作研究中心主任彭慶華告訴記者,粵劇的美不是追求“靚”,而是要符合角色、人物、形象、行當(dāng)、劇情,是賞心悅目而不是嘩眾取寵。粵劇戲服是一部“字典”,它以明制服裝為基礎(chǔ),觀眾看到戲服,就能區(qū)分誰是文官誰是武將。有的業(yè)余發(fā)燒友,過于追求“美”忽略角色行當(dāng)要求,穿著大靠做文官的戲。“演員不可以穿錯(cuò),演員要對(duì)自己的戲講究,要當(dāng)自己是一回事”。
○舞臺(tái)
▎廣東舞美機(jī)關(guān)布景曾全國首屈一指
僅一桌二椅,就能幻化出“江湖河海”;走一圈圓臺(tái),已走過了“千山萬水”。粵劇之美,與京劇、昆曲等傳統(tǒng)戲劇一樣,在于其抽象和高度凝練的表現(xiàn)方式。羅麗告訴記者,傳統(tǒng)粵劇一般采用“一桌兩椅”的舞臺(tái)裝置,沒有布景,即使有,也是簡單的、帶有刺繡的布幕一塊。
隨著時(shí)間推移,粵劇的布幕變成了布景畫。這些布景畫不是傳統(tǒng)國畫,而是使用西洋定點(diǎn)透視法畫成、帶有立體感的風(fēng)景畫。由于廣東得海洋風(fēng)氣之先,留洋取經(jīng)者眾,廣東舞美機(jī)關(guān)布景彼時(shí)在全國首屈一指,連梅艷華也曾花重金請廣東畫家馮康侯上京設(shè)計(jì)舞美。
粵劇的舞臺(tái)裝置藝術(shù),與粵劇服裝經(jīng)歷了相似發(fā)展歷程,在追求“華美”“新奇”的過程中一度失去了抽象美與具象美的平衡,但不得不贊嘆的是,當(dāng)時(shí)粵劇舞美師吸納新科技時(shí)的勇氣,這種對(duì)藝術(shù)形式的創(chuàng)新,至今仍在粵劇的靈魂中。
洪三和是另一位擅長制作舞臺(tái)特技的舞美設(shè)計(jì)師,他年輕時(shí)曾在上海學(xué)習(xí)布景繪畫,喜愛“海派”風(fēng)格布景的粵劇名伶靚少佳在上世紀(jì)20年代禮聘洪三和為劇團(tuán)的布景師。
此時(shí),圣壽年班正在抬舉新扎花旦郎筠玉。洪三和為郎筠玉《穆桂英》一戲設(shè)計(jì)舞臺(tái)時(shí),使出海派絕招:將舞臺(tái)臺(tái)板上鑿一個(gè)洞,豎起一根巨大的、會(huì)旋轉(zhuǎn)的、閃閃發(fā)光的“降龍木”。大幕一開,即令觀眾嘆為觀止。
在《薛蛟斬狐》一劇中,洪三和祭出了新招,當(dāng)劇中狐貍精吐出狐珠時(shí),天幕上閃出無數(shù)滾動(dòng)的珠子,并逐漸凝聚成一顆五光十色的明珠,情景交融,令觀眾連連喝彩。
洪三和還為白玉堂、芳艷芬設(shè)計(jì)了《夜祭雷峰塔》,在舞臺(tái)上暗接了一個(gè)花灑,水流噴出,演員就在雨簾后表演。
“粵劇的特點(diǎn)、優(yōu)點(diǎn)、缺點(diǎn)都在于變。那個(gè)時(shí)候的舞臺(tái),會(huì)下‘真雨’,甚至?xí)砍觥骜R’,這些都違背了粵劇中對(duì)抽象、寫意的審美。建國后,粵劇舞臺(tái)藝術(shù)返璞歸真,還吸收了嶺南畫派藝術(shù)的精華,更樸實(shí)更實(shí)用,往提供戲劇環(huán)境的路線走。”羅麗說。
參考書目:《粵劇大辭典》
文:廣州參考·廣州日報(bào)記者方晴廣州參考·廣州日報(bào)編輯程依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