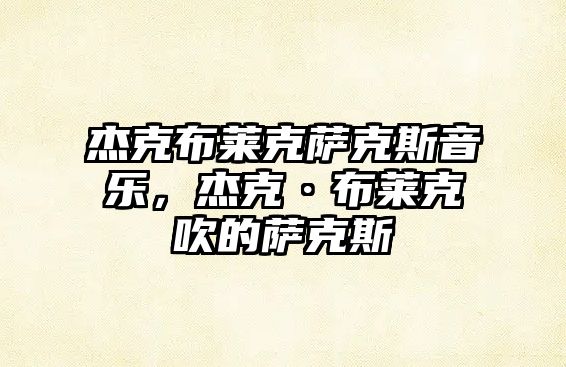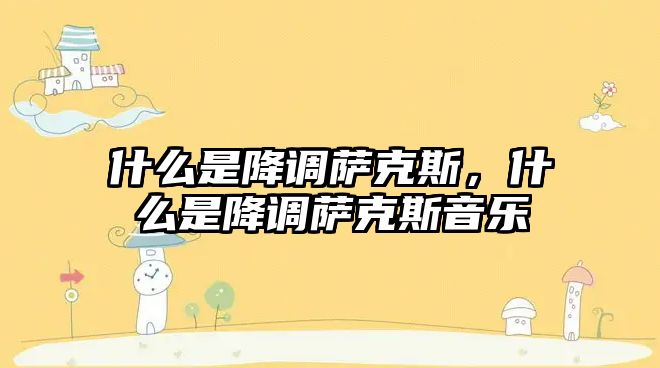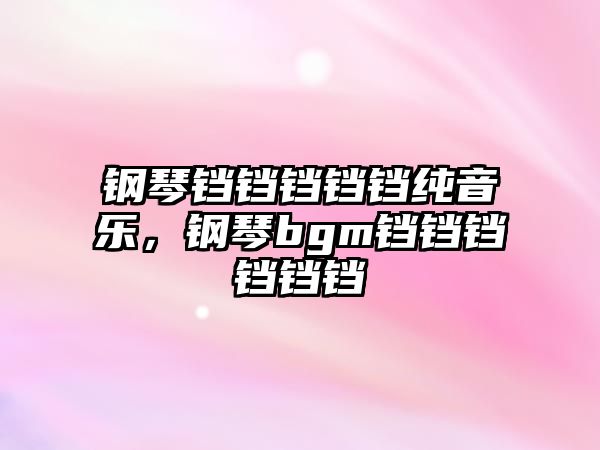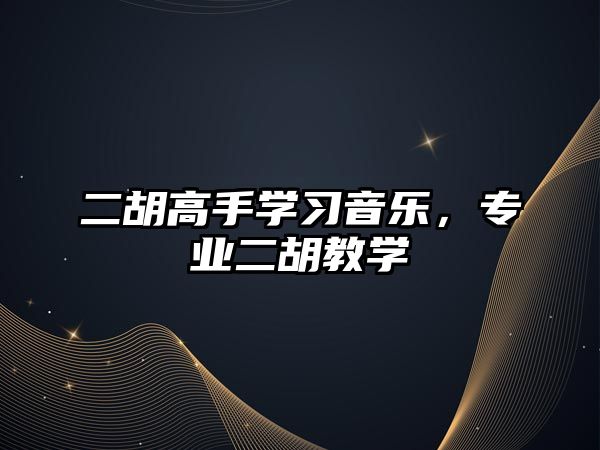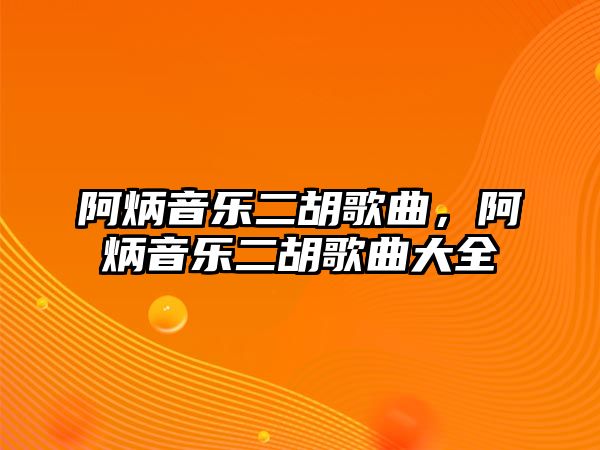江陰薩克斯紅歌(沁心繞夢 江陰時刻)

得山川之助,倚江海之達!江陰一日,既欣賞了“城邊山色翠屏風”的美景,曠遠如敔山灣,精致如黃山湖;又感悟了“直掛云帆濟滄海”的豪氣,那從媒體融合的時代變革中而生。
“變——變局勢,應變、巧變、轉變;強——強流程、突出移動優先,強技術、建強全媒體生產指揮平臺,強‘四力’、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闖——闖市場,帶著優勢闖,帶著支持闖,帶著數據闖;聚——聚人才,靠情懷聚,靠事業聚,靠文化聚。”江陰市融媒體中心王敏主任如是說,一番話,讓人看到了未來,又似觸摸到了理想。
在這一個全省融媒體中心建設推進會上,我的心游弋在夢里——既在感懷過去,又在凝望未來。
“如智者般思考,如農夫般細作,如戰士般勇敢。”這三句概括融媒人品質的話,在這位優雅的女主任的身上似隱似現。尤其欣賞“如農夫般細作”,記得數年前我離開一家新聞單位時講了這一句話:“我是個安心做事的人,信奉的是腳踏實地。我覺得人生最靠譜的是一天一天的堅守,一點一滴的積累。”
會間,小憩的我被兩位年輕的新媒體記者攔下,說要采訪我。我答應了,沒有絲毫猶豫。記者心懷欣喜,畢竟一些人不愿意出鏡,她們守得好辛苦。而我,也是從一線普通記者做起的,品嘗過記者的酸甜苦辣,就配合著露一下臉吧。我說:“……媒體融合,最重要的是能否占領移動互聯網的市場。”

“頭發這么白了啊!”“那么多年歷練造就了你的氣場!”待那《江陰時刻》視頻號推送時,引來眾多朋友關心。
其實,我講的是一個關乎媒體生死的大事。在媒體格局巨變的時代背景下,即使如激情昂揚的王敏主任,演講最后也引用了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二圓舞曲》,以及他的話:“我們依然活著,我們必將勝利!”
肖斯塔科維奇的配器不傾向于色彩性的渲染,而著力于戲劇性的刻畫,一件件樂器成為故事中的角色,推動著“劇情”的發展。這首《第二圓舞曲》,清新明快的旋律裹挾著一縷別人察覺不到的憂郁與傷感,低吟的薩克斯管,歡暢的弦樂,恍如演繹著一場愛恨離愁……唯有那顆不甘的心,在喧騰的舞會上懷念著逝去的美好!
對于媒體融合來說,勝利則很遙遠,所幸活著。把握住現在,才能擁有未來!而對于媒體人來說,如今更需要的是被認同感,努力追求的是記者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我的心底,想起的則是另外一首樂曲,去年9月,我又一次離開媒體前,做了最后一期“聆聽古典”,選擇的是阿沃·帕特的《鏡中鏡》。
曲已終,人已散,就是那曾經的“你早啟東”,也已了無蹤影。匆匆的腳步里,唯剩一個夢,一個游弋在慢時光里的夢!

阿沃·帕特:《鏡中鏡》游弋在慢時光里的夢
未曾擁有,就不會告別
未曾告別,就不盼相聚
時光,一條簡約而神圣的河
緩緩流動,樂音依稀
任它消磨了青春
流水,一面照見皺紋的鏡子
也照亮你的聲音,綿綿無絕期
對著鏡,像得到更像失去
別了!于寂靜中回歸孤獨
卻在孤獨中守望永恒
喜歡你聆聽的樣子
如同,仰望一片云
站在記憶的對岸
云,是自由飛翔的你
聆聽阿沃·帕特的《鏡中鏡》,感受的是分別,體悟的是寂靜。
青春,愛情,夢想……一切的美好,在這音樂里似乎變成了曾經,你在和自己所擁有的一一告別。
遠離塵世的喧囂,接近本真的心靈,思緒順著柔和緩慢的音律自由自在地流淌。于靜寂的氛圍中聆聽恒久的樂音,任故事開始與結束;于孤獨的思考中重新認識自己,梳理過往的愛與非愛。
漸漸地,會有一股原始的力量悄悄萌芽,在自己的心頭潛滋暗長。是思念?或是新生的淡定的愛——一種擁抱生活擁抱未來的力量。
許多時候,我們需要這樣一次心靈的孤獨之旅,給時光一個清淺的回眸,輕輕放下,再去趕自己的路。
這就是我選擇分享《鏡中鏡》的理由,在悅聽越好聽·古典音樂的最后一期。

其實,先后有二十多部影片、舞蹈選用了這首樂曲作為配樂。2019年的六月,梅雨之季,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美國舞臺布景設計大師RobertWilson(羅伯特·威爾森)的主題珠寶展上,一艘小船代表了諾亞方舟,方舟則幻化成內裝珠寶盒的大型黑盒,進入方舟內部,持續播放的影像讓人聯想起浩瀚的大海,耳邊縈繞的是《鏡中鏡》的音樂……
我沒有去參觀,但想象得出,那樸素的音樂所營造的一片靜寂而奇幻的氛圍,以及在愛慕與舍得之間蕩漾的詩心禪意。
鋼琴反復奏出分解三和弦,像微風拂過空曠的原野,回蕩著寂寥的鐘聲;提琴悠緩地拉出一條條綿長的和弦音,恍若漆黑的夜空中閃過一顆流星,劃出一條美麗的弧線,又映在心上,一遍遍地回放。那或許是一種虛幻的景象,卻因為美麗讓我們一次次懷想,繼而沉思——所有美好的事親愛的人都會悄悄涌上心頭,又靜靜地隱入記憶之湖。
《鏡中鏡》是“神圣簡約主義”作曲家阿沃·帕特流傳最廣的作品之一,樂曲為鋼琴和提琴而作,有三個版本,分別是鋼琴與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組合(后來的演奏中甚至還有弦樂四重奏的版本);二聲部的對位中,一個聲部演奏三和弦,另一聲部如影隨形,固定聲部和移位聲部相互交織。聆聽音樂,那鋼琴演奏的“鐘鳴”聲總是在低音區轟鳴,而提琴演奏的音樂主題在無盡的時空里緩緩游弋……
越是簡單的音樂越不容易寫,很可能失之于單調、蒼白、重復、抄襲。阿沃·帕特為他的音樂表達創立了“鐘鳴作曲法”(tintinnabuli,拉丁語,小鈴鐺),一種看似簡單,實則需要經過精密設計,有著嚴密內部邏輯的技法。他的唱片上這樣解釋:回到最簡單基本的三音和弦,以調性和聲為基石,但抽去了調性體系的功能,使之失去方向,類似中古音樂那樣的平行級進。
“我使用盡可能少的元素,只有一到兩個聲部,將音樂建構在最原始質樸的素材上——三和弦,一種特殊的調性音樂。”阿沃·帕特說,“在我生命低谷的黑暗中,我似乎感覺一切都是外在而毫無意義的,紛繁復雜的面貌令我困惑,我定要尋求一個統一……三和弦的三個音就像鐘鳴,它很接近我心中的那個完美之物了。”

阿沃·帕特出生于一戰后獲得獨立的愛沙尼亞,這個國家先被蘇聯吞并,后被德國占領四年,之后四十五年里成為蘇維埃加盟國。動蕩的國運勾連的是作曲家漂泊的人生,1980年,他舉家移民遷居柏林。
從師法肖斯塔科維奇與普羅柯菲耶夫,創作出新古典風格作品;到傾向于先鋒音樂,寫出十二音作品《死亡名冊》(Nekrolog),而被官方視為危險人物;再到經歷創作危機、潛心研習復調音樂,向古代大師汲取靈感,最終創立了鐘鳴作曲法。阿沃·帕特走的是一條返璞歸真的音樂創作之路,那是與現代生活軌跡相反的一個方向。他說,我需要后退來描畫某些物體,我們越陷入混亂,越要堅守秩序。阿沃·帕特的后退應是一種守望,退到歷史的深處來審視現代世界。
《鏡中鏡》創作于1978年,那一年作曲家43歲,兩年后離開蘇聯,其時他的生活我們無從知曉,但感覺得到他所承受的壓力。阿沃·帕特的傳記作家保羅·希利爾說:“他(阿沃·帕特)完全失落到覺得音樂最無用,連寫一個音符的信心及意志也沒有。”這或許是一種夸張的說法,但他正在痛苦的審視中開始音樂創作的轉型,直至探索出了鐘鳴作曲法。《鏡中鏡》應是作曲家躲在幽暗的角落里審視家國命運的結果,也是審視自我創作的結晶。
“我將我的音樂比作包含有五顏六色的白光。只有多棱鏡能將各種顏色區分并顯現出來;聽者的精神世界就是這個多棱鏡。”阿沃·帕特說。

鏡中之鏡,夢中之夢!對于聽者而言,那是對著鏡子的審視,也是囿于夢中的向往。回眸,映出一片黑白的記憶;前望,折射出一個多彩的世界。
聆聽《鏡中鏡》,可以貼上憂傷的標簽,鋼琴和提琴好似兩條游來游去的魚,相濡以沫也好,相忘江湖也罷,在那時間的長河里,瞬間就是永恒,唯求相遇時的靈犀一點,閃耀著生命的光芒;
聆聽《鏡中鏡》,也可以注入沉思的內涵,音樂無窮無盡的律動與延伸中,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漠,一步一步艱難前行,沒有了方向,沒有了依靠,可一回頭,注視那深深淺淺的腳印,仿佛又明白了自己從哪里來,更清晰了自己要往哪里去;
聆聽《鏡中鏡》,更可以萌生向往的力量,起起伏伏微微搖擺的旋律,像是在云海里飄搖一般,平靜而自由,你擺脫了世俗的羈絆,也拋棄了塵世的煩惱,簡單生活,簡單愛,游弋在慢時光里,去追求那一個純凈的夢境……
或許悟了:十方所有諸變化,一切皆如鏡中像。
但透過鏡中之鏡,照見真實的自我,照見逝去的歲月,照見孤獨的堅守,你至少懂得了:珍惜!
圖文:木火
主播:馨悅
圖片攝于江陰敔山灣、黃山湖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