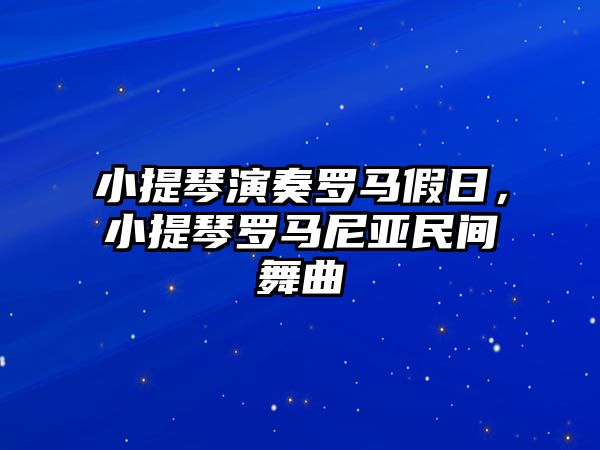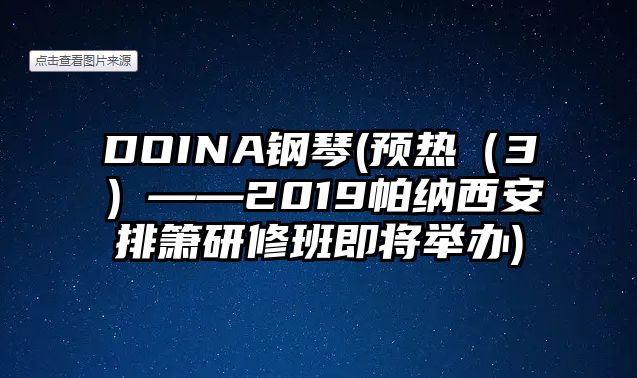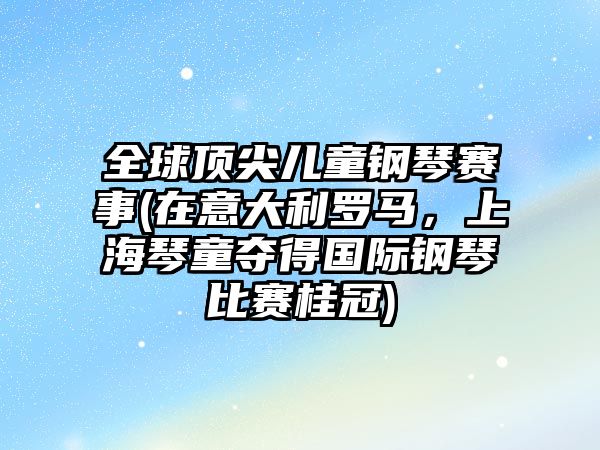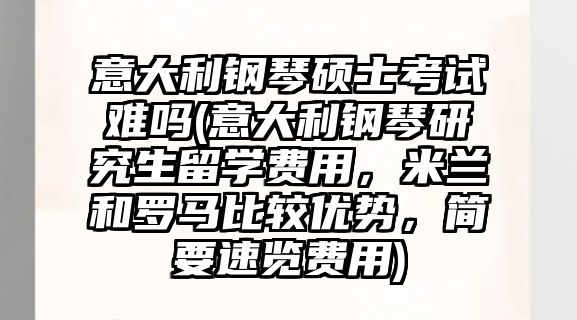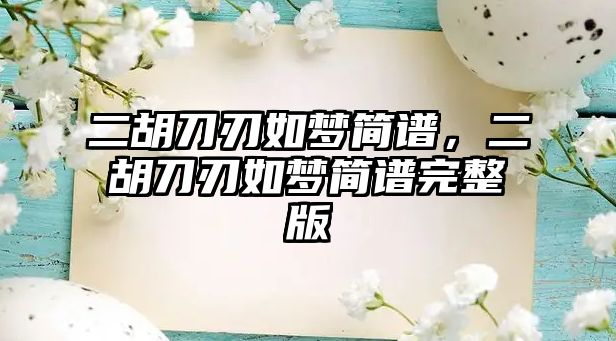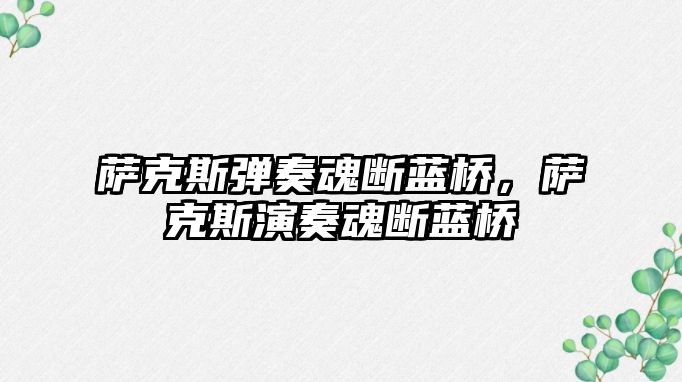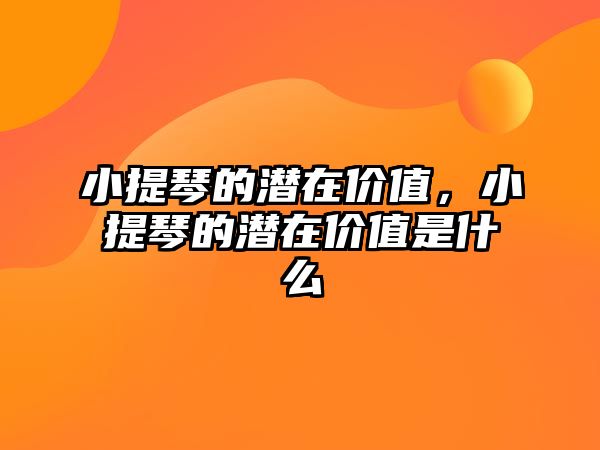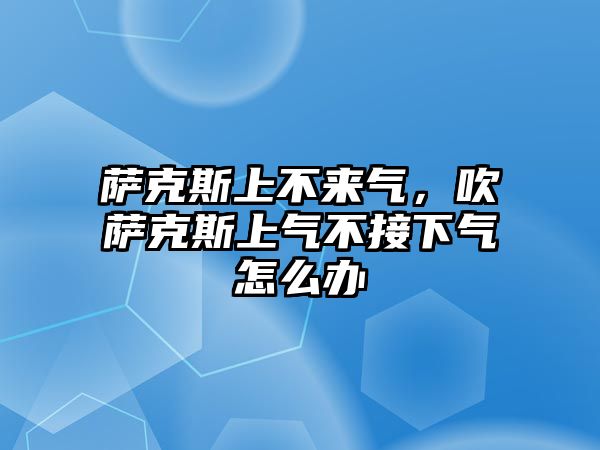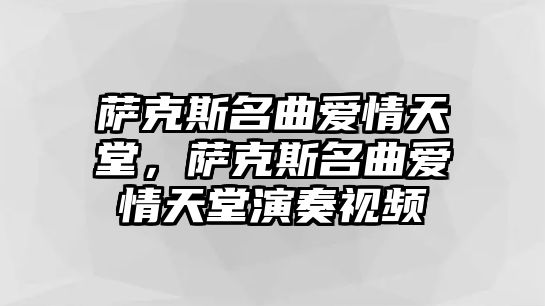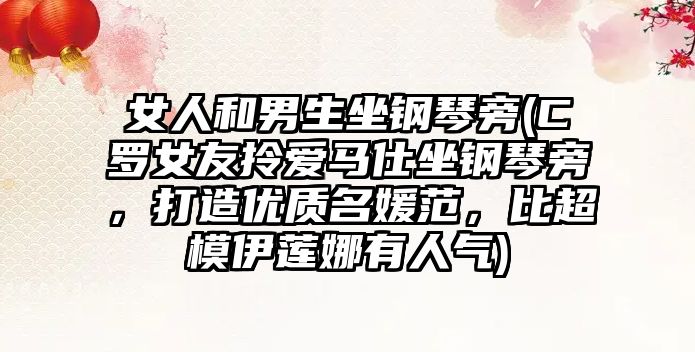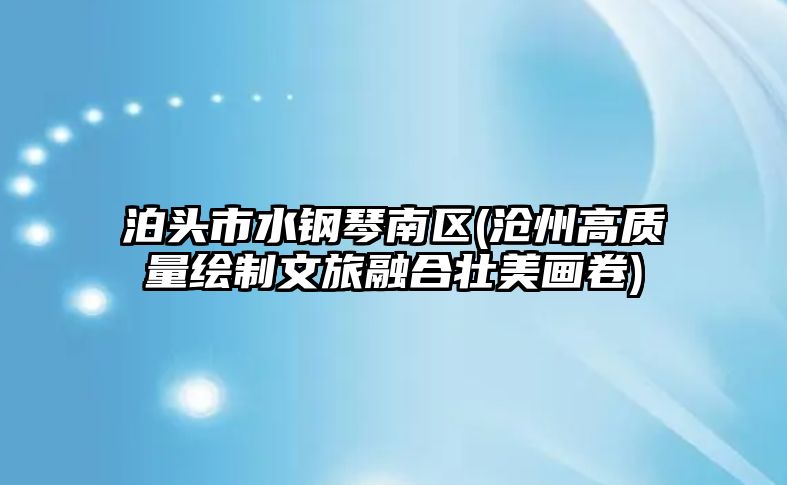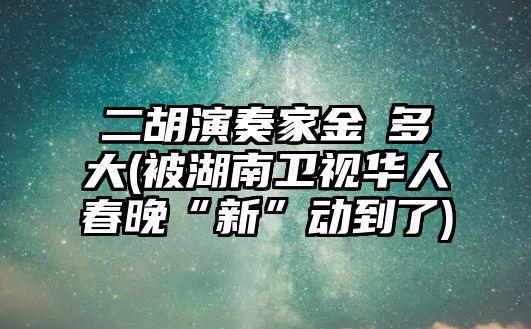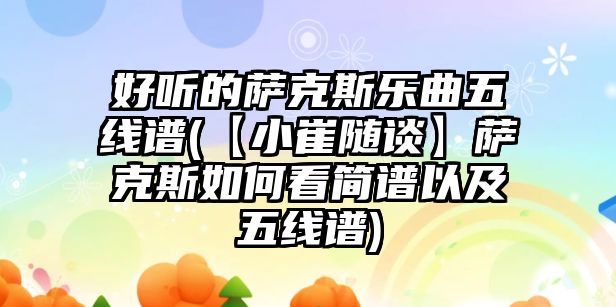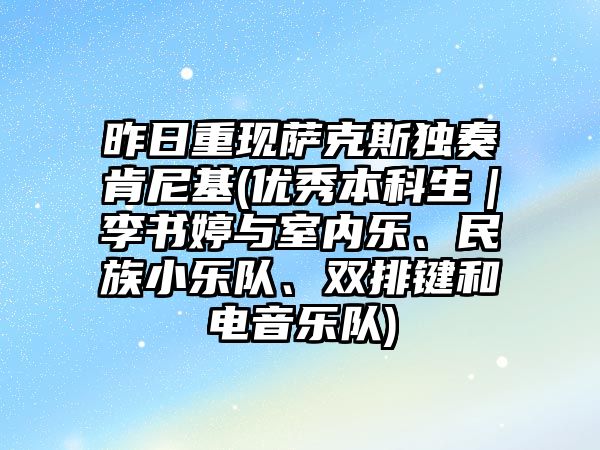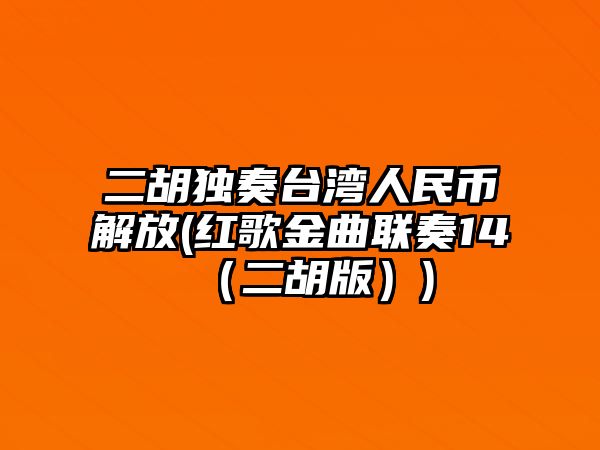小漠解說薩克斯(暗藍評《命令已經執行》丨記憶之戰與共同體的重生)

《命令已經執行:羅馬納粹大屠殺的記憶之爭》,[意]亞歷山德羅·波爾泰利著,張見微譯,2023年7月出版,584頁,118.00元
2023年3月24日,為紀念阿爾帖亭洞窟屠殺慘案發生七十九周年,意大利現任總統塞爾焦·馬塔雷拉等人出席了在羅馬郊外舉行的哀悼儀式。然而并未出席這一儀式的意大利現任總理、右翼聯盟意大利兄弟黨主席焦爾吉婭·梅洛尼的致辭卻引發爭議。當她表示“這次大屠殺是我們國家所遭受的最深痛的創傷之一:三百三十五名無辜的意大利人僅僅因為他們是意大利人而遭到屠殺”,多位意大利政治人物第一時間抨擊了這一言論。“不,梅洛尼總理,三百三十五人在阿爾帖亭洞窟被屠殺并不只是因為他們是意大利人,”綠色左翼聯盟議員尼古拉·弗拉托揚尼在推特上寫道,“因為他們是意大利人、反法西斯人士、猶太人、游擊隊員,反法西斯(ANTIFASCISTA)才是關鍵。”(相關原文引自安莎社[ANSA]2023年3月24日報道:FosseArdeatine,Meloni:"335italianiinnocentimassacratisoloperchéitaliani".Anpieopposizioniattaccano)
盡管阿爾帖亭洞窟的硝煙早已散盡,但幾十年間,圍繞這一悲慘事件的爭論與爭議始終未曾斷絕。其中既有如梅洛尼總理發言引出的受害者身份問題,亦有濫用這一事件的細節煽動仇恨情緒的惡劣做法,如2007年12月意大利政客吉奧喬·貝蒂奧在談論移民問題時公開表示,“若移民傷害意大利公民,我們不妨采取納粹黨衛軍當年的手段,讓他們以十抵一”(路透社[Reuters]2007年12月5日報道:ItalypoliticianurgesNazipoliciesforimmigrants)。他談論的正是納粹炮制阿爾帖亭洞窟屠殺所遵循的報復命令——當1944年3月23日意大利抵抗組織“愛國行動組”發動襲擊,造成三十三名德國人傷亡,納粹司令部隨即宣布“以十抵一”,這才有了不到二十四小時后三百三十五名受害者的暴死。
基于此,原書出版于2005年的《命令已經執行》時至今日仍未過時。“這兩個(發生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的)事件以及對其記憶和意義的爭奪,揭示了羅馬的歷史和身份、意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沖突,以及武裝抵抗的倫理問題。”(第3頁)關鍵在于,納粹方面針對抵抗運動的報復來得如此迅速,然而血債血償的邏輯從來都不會帶來終結,而是撕裂的展開與延續。暴死與屠殺的無差別性意味著死亡不再歸屬于個人,進而使得切實的悲劇淪為景觀,為公共場域中的眾人所爭奪甚至褻玩。而本書作者亞歷山德羅·波爾泰利通過大量口述史料重述這一事件本身及其余緒的努力,正是為了將意義還給個人。從學術角度上說,波爾泰利繼承了自《奶酪與蛆蟲》以來的微觀史傳統,然而對他自己——“皮洛·阿爾貝泰利這位最著名的受害者曾是我母親的哲學老師;而我家的房子,正是建在另兩位受害者馬里奧·卡佩奇和阿爾弗雷多·卡佩奇小時候追逐打鬧的那塊場地之上……我班上的一個女孩,她的祖父就死在阿爾帖亭”(10頁)——而言,這是他務必拾回的歷史碎片。唯有當個人的真正歸屬個人,我們才能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才能讓共同體真正成立。
羅馬,不設防的城市
由“愛國行動組”策劃并執行的拉塞拉路炸彈襲擊以及接踵而至的阿爾帖亭洞窟屠殺,發生在“不設防”狀態下的羅馬。根據1907年《海牙公約》,在戰時狀態下,當一座城市宣布“不設防”,進攻一方可以和平占領該城,但不得采取任何方式對其進行攻擊。二戰期間包括巴黎在內的多座城市都曾宣布進入“不設防”狀態,但隨著意大利導演羅西里尼于1945年拍攝的影片《羅馬,不設防的城市》(Roma,cittàaperta)作為新現實主義電影的開山之作被奉為影史經典,羅馬幾乎成為這一概念的代表。影片并未直接討論何為“不設防”,但通過表現二戰尾聲德軍占領下羅馬城民眾的生活及其抵抗,“不設防”背景下的平民意志得到充分升華,集中體現便是片尾因協助抵抗人士被捕、慷慨赴死的神父的遺言,“死并不難,難的是負重生活”——在他身后,是一群孩子互相攙扶著離開行刑地,他們將帶著沉重的記憶迎接勝利與新生活。

《羅馬,不設防的城市》中國海報
然而現實總要復雜一些。1943年8月14日,在遭受盟軍第二次猛烈轟炸之后,意大利巴多利奧政府——墨索里尼政府在同年7月25日剛被推翻——宣布羅馬為“不設防的城市”,希望該城可以免受盟軍與德軍雙方軍事行動的影響。然而盟軍并未接受這一聲明,德軍則在9月11日占領羅馬后,宣布羅馬為“戰爭領土”,并在9月23日派出空降軍突襲羅馬城市總部,逮捕了守軍司令卡爾維將軍。換言之,“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始終只是一廂情愿的主張,作為“一座被占領的城市與自己過去脫鉤的口號,卻從未得到盟軍承認。德國人也從未如此對待羅馬,而是將其當作開往前線的車隊的中轉站、德國士兵休整的地方,以及為戰壕和德國工業提供勞動力資源的人礦”(174-175頁)。
“不設防”換來的只是更進一步的傷害與屈辱,這便是阿爾帖亭洞窟屠殺的背景,也是羅西里尼的電影不曾直接表現的部分,盡管片中的主角如神父身上顯然有多位曾參與地下軍事組織,日后被捕就戮的羅馬神職人員的影子(如死在阿爾帖亭洞窟的彼得羅·帕帕加洛神父、在布拉韋塔堡被處決的朱塞佩·莫羅西尼神父)。抵抗是被動的反應,然而無論是在當時還是日后,都會被定義、想象成主動的選擇:
是的,如果能在死后知道他為何把炸彈扔在拉塞拉路,當然好。他說“我讓意大利恢復了尊嚴”。他在說什么呢?羅馬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市。——利亞娜·吉廖齊
朱塞佩·博爾賈羅馬,這座不設防的城市,既不被美國人,也不被德國人尊重——事實上,我們是他們的奴隸,僅此而已。你是什么意思,要來統治羅馬?你是誰,希特勒——世界的主人?他們把我們當作奴隸,你不能說話,一個字都不能說,如果你聽了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那就糟了。什么都是秘密,一切都應化作沉默。生活就是恥辱,加上饑餓和貧窮。我們每天只吃一百克面包。買土豆的隊伍很長,買燒飯用的煤也要排長隊。然后是對另一次空襲的恐懼,在第一次空襲之后,我們像地鼠一樣奔跑,害怕被埋在廢墟下……(173頁)
利亞娜是阿爾帖亭洞窟大屠殺受害者羅莫洛·吉廖齊的女兒,朱塞佩是另一位受害者米凱萊·波爾賈的兒子——他的母親死于1943年7月19日盟軍的空襲。羅馬人別無選擇,他們的生活被德國人占領,而他們的天空亦被遮蔽。在令人窒息的雙重威脅之下,抵抗運動與其說是為了虛無縹緲的勝利或是尊嚴,不如說只是為了“上來透口氣”(喬治·奧威爾語)。拉塞拉路的爆炸是對無從反抗的暴力的反饋——然而在真正承受暴力的人們開口言說之前,旁觀者從未接受這一理由。
歷史,延續萬年的丑聞
所以旁觀者接受的是怎樣的理由呢?如果把拉塞拉路的襲擊視為英雄之舉,那么阿爾帖亭洞窟的屠殺便是邪惡的反撲——要完成一出偉大的悲劇,殉道者自然必不可少:
《羅馬觀察報》將阿爾帖亭洞的死難者描述為“被犧牲的人”。從那一刻起,犧牲和殉道的隱喻就主導了回憶的聲音。1944年的進步雜志《信使》專門介紹了羅馬被占領的情況,其中一位署名F.G.的作者寫道:“充滿恐怖的黑暗的日子,因英雄的犧牲之光而略顯明亮。”然后,他將阿爾帖亭洞窟的死者同躺在羅馬周邊鄉村地下的圣徒和殉道者聯系起來。(332頁)
將屠殺所帶來的死亡神化成“犧牲與殉道”,使之成為某種隱喻上的紀念碑,從而免受時間的影響,這樣的做法常見且看似無可厚非。然而神化這一動作本身便隱藏著意義偏移的危機:“……‘被犧牲了’,仿佛他的圣潔來自謀殺他的人。……另一方面,當受害者被賦予一個積極的角色時,他是一個自愿的祭品。甚至在最高尚和最真誠的版本中,殉道者的形象也傾向于將謀殺變成禮物。”(335頁)死者正是以這樣的方式與生者隔離開來,而屠殺反倒成了他們雖悲慘但必須承受的命運。
我們當然不難看出其中的荒唐,然而將悲劇英雄“凈化”——去人性化,始終是合理化犧牲的必要手段,而犧牲合理則意味著人們必須哀慟,一個人為的共同體便由此形成。然而正如卡內蒂指出,哀慟群體始終遵循“具有本質意義的兩種運動趨勢:第一是奔向臨死者的激烈運動,并在處于生存和死亡之間的人周圍形成莫名其妙的一堆人;第二是充滿恐懼地逃離死者,逃離死者和一切可能與死者有關的東西”([英]埃利亞斯·卡內蒂:《群眾與權力》,馮文光譯,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58頁)。這樣自上而下號召而形成的團體,自下而上卻存在無數裂痕。于是阿爾帖亭洞窟長時間都只是一座矗立于記憶荒漠的大教堂,宏偉但無人問津——“在羅馬,有四十六條街道被冠以阿爾帖亭洞窟大屠殺受害者的名字……然而,‘在為紀念烈士而以他們名字命名的街道上,卻從來沒有一個花圈或一束鮮花’”(411頁)。真正的哀悼只存在于相關者身上,正如戰爭與屠殺只能通過毀滅個體傷害群體——而非相反:
“我們從不說‘阿爾帖亭洞窟’;我們只說:‘我去給爸爸送點花。’”(朱塞平娜·費羅拉)自從圣母大殿的“暴亂”發生以來,對死者的公開占有(appropriation)就可能變成一種征用(expropriation)行為:“那些官方儀式和軍事色彩的東西讓人厭惡,又是舉槍致敬,又是軍隊神職人員出席,更不要說那些夸夸其談的演講……”(克勞迪奧·法諾)“有一些人為的東西,比如遮篷之類的;這讓我很生氣,我告訴母親,‘不,我不是來聽這些小丑講話的;我只想和我父親待在一起,我會和他們[這些死者]交心,向他們學習’。”(蘿塞塔·斯塔梅)(413頁)
然而通過“征用死者”構建哀慟群體尚且不是銘記阿爾帖亭洞窟屠殺最糟糕的方式。實際上自事件發生以來,一種爭議便長期存在,即若無襲擊便無屠殺——德軍所執行的“以十抵一”的命令本身其實具有某種合理性。這種記憶由德占時期的新聞報道初步塑造,又被日后的意大利右翼政客所利用,用以“清除反法西斯‘偏見’”(19頁)。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如貝盧斯科尼政府副總理詹弗蘭科·菲尼)也許會肯定抵抗組織的行動本身,但同時也堅持認為是他們帶來了屠殺——如果他們主動自首,報復命令便不會執行,無辜的平民便不會卷入災難。甚至人們的記憶也隨之出現偏差:當本書作者波爾泰利向幾十個出生于不同年代、社會教育背景與政治傾向亦不盡相同的人士提問拉塞拉路襲擊與阿爾帖亭洞窟屠殺之間隔了多久,得到的答案從兩天到半年不等,平均為兩周,而正確答案是不到二十四小時。抵抗組織成員根本沒有時間自首——換言之,正如阿達·皮尼奧蒂(她的丈夫、夫兄、丈夫的表哥、夫兄的外甥都在阿爾帖亭洞窟遇害)所言,“是的,是有襲擊;但這就是回應的方式?你們就不能至少花點時間去找襲擊者?不,你們只是去開槍”(268頁)。
事實證明,哪怕是面對最愚蠢、最荒唐的“命令”,人亦有將它合理化的傾向,而記憶的機制更是如此。“民眾信念中的這種時間的拉長,是有關這兩個事件的最迷人的記憶結構。它最直接的后果是,通過想象納粹有時間對游擊隊員發布呼吁,加強游擊隊員有罪這一信念。”(269頁)如果我們把這種通過蓄意引導和無意識重構的記憶稱之為歷史,那么它的真相其實已經由參加過抵抗運動的意大利作家艾爾莎·莫蘭黛寫在了她的書名里:《歷史,延續萬年的丑聞》(LaStoria,Unoscandalocheduradadiecimilaanni,1974)。“在茍且的歷史面前,見證者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徹底病倒,也就是成為丑聞不可救藥的同伙,要么徹底康復——因為正是在看透了極端的茍且之后,才能學會純粹的愛情……”([意]艾爾莎·莫蘭黛:《歷史》,萬子美等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0年,761頁,譯文據英譯本有改動)

阿爾帖亭洞窟入口
烏鴉,最后到來的預兆
阿爾帖亭洞窟的記憶之戰只是一個縮影。它所表現的共同體(community,一譯“共通體”)的撕裂是“奧斯維辛之后”(NachAuschwitz)的普遍現實——當阿多諾言及寫詩的野蠻,他也許并不是在說浩劫之后“抒情言志”有何冒犯,而是人們已經喪失了理解詩歌的共同心靈基礎。強與弱、左與右、抵抗占領與執行命令——一切都在趨向絕對。“這個(絕對的)邏輯將會是這種簡單而可怕的邏輯,它蘊含著:絕對被分離的東西在它的分離之中封閉著——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不僅僅是簡單的被分離的東西。這就是說,分離本身就必須被封閉,閉合不應該僅僅圍繞著一塊領地……而是為了完成分離之絕對性而圍繞著閉合本身。”([法]讓·呂克·南希:《無用的共通體》,郭建玲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頁)
或許同樣曾經參加過抵抗運動的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早已想到——并受困于——這一點。194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通往蜘蛛巢的小徑》。作品取材自他參加抵抗運動的經歷,然而卻刻意避開了當時文學界構建記憶的“主流使命”,“我虛構了一個寫在游擊戰爭邊緣的故事,與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無關,卻傳遞了它的色彩、節奏、辛酸的味道……”([意]伊塔洛·卡爾維諾:《通往蜘蛛巢的小徑》,王煥寶、王愷兵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9月,17頁)
是的,“色彩、節奏、辛酸的味道”,這些才是“大歷史”(History)碾過眾人之后,所能留下的唯一真實的“小歷史”(history)。卡爾維諾的主人公少年皮恩完全無法理解大人世界殘酷的戰爭與政治,只記得自己參與了一次并不好玩的冒險,到最后“沒有人能還給他手槍了……皮恩一個人留在世界上”(同上,162頁)。而阿爾帖亭洞窟的幸存者(大部分是遇難者的后代)何嘗不是如此:
西爾維奧·吉廖齊這是我父親的遺物:一顆牙齒。它的一側壞了,因為我父親曾試圖用這顆牙齒咬碎一枚堅果,而我母親正是從這顆一側壞了的牙齒認出了父親的尸體。這就是我父親的遺物。
蘿塞塔·斯塔梅[在這個甕里]我保留了爸爸的一些東西。看看他的頭發。我們搬家的時候玻璃碎了,我打開來摸了摸——它還活著,你知道我的意思,還活著……這是他的外套的一角:如果你看一下手帕,還能看到血跡。他的十字架和指甲刀都在塔索路[的博物館],還有他脖子上戴的一個小勛章。然后有一塊是他的大衣;這個綠色的東西是他的襪子。這些則是他制服上的星星。看看這些污點?都是血。然后我拿了一個小瓶,在里面裝了一些土。(324頁)
“我們唯一擁有的真實是敘事真實,是我們對彼此訴說也對自己訴說、不斷被重新歸類和提煉的故事。”([英]奧利弗·薩克斯:《意識的河流》,陳曉菲譯,北京聯合出版社,2023年,128頁)個體的聲音之所以珍貴,是因為那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真實,“人性的、太人性的”遠比臆造的絕對性更能實現共契。也正因如此,時至今日,當阿爾帖亭洞窟屠殺的歷史線索已近模糊,無法被年輕一代掌握,這場曠日持久的記憶之戰反而迎來了轉機:
多虧年輕的無知,以及與過去隔著距離,許多年輕人無法做到這一點,或者對這樣做不感興趣。這樣,他們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本身,而非環境和原因之上。哪怕將阿爾帖亭洞窟與滅絕營錯誤地聯系起來,也有助于他們把它視為一場毫無意義的屠殺,想象其中赤裸裸的荒謬(“就處決本身而言”)。“我可能不太關心具體死了多少人或者準確的日期;我想說的是這種行為的荒謬性,你知道嗎?它所使用的暴力,以及它所執行的戰爭法則的荒謬性,什么每有一個德國人被殺就要殺掉一定數量的人。這才有這么多人被殺。”(羅薩·卡斯特拉)“我更關心的是——我之前說過他只是個小男孩,曼弗雷迪·阿扎里塔——人們的感受。因為我們清楚事實,知道遇難者人數多五個或少五個并不重要,問題不是有沒有算錯五個——問題是:人。”(米里亞姆·蒙達蒂)(503-504頁)
“荒謬當道,愛拯救之。”([法]阿爾貝·加繆:《加繆筆記:第一卷》,黃馨慧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107頁)荒謬的盟友是死亡,亦是死亡提醒我們應該相愛。在短篇小說《烏鴉最后來》(Ultimovieneilcorvo,1946)中,卡爾維諾讓筆下的士兵玩了一個游戲:他漫步田園詩一般的鄉間,舉槍射殺了松鴉、睡鼠、蘑菇、蝸牛,“這樣從一個目標過渡到另一個目標真是一個有趣的游戲:也許這樣就能周游整個世界”([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短篇小說集》,馬小漠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4月,64頁)。然而當一只烏鴉飛過,他卻怎么也打不中了——這次士兵成了其他人的獵物。作為死亡的象征,烏鴉最后來——所有殺戮與奪取的游戲都將以此作結,而它也預示著被野心撕裂的共同體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