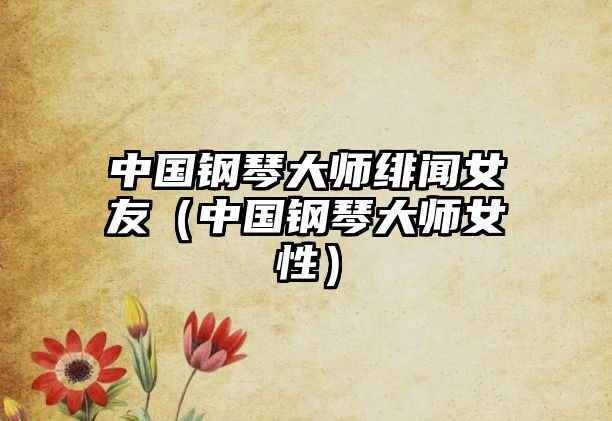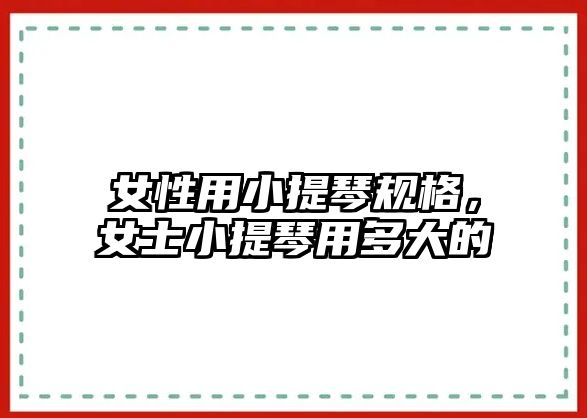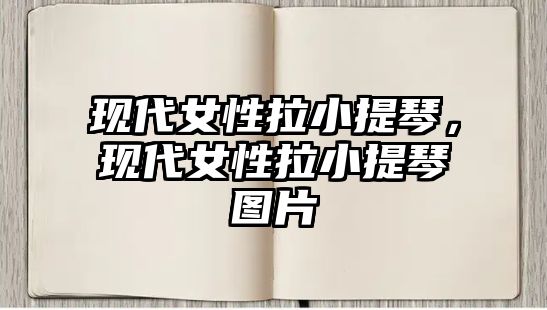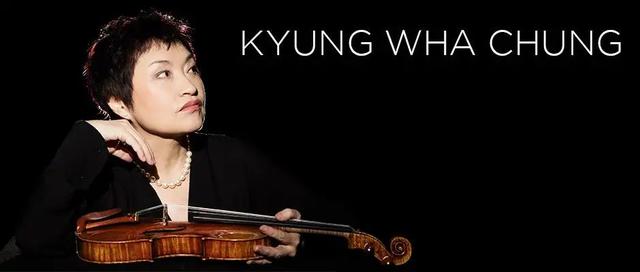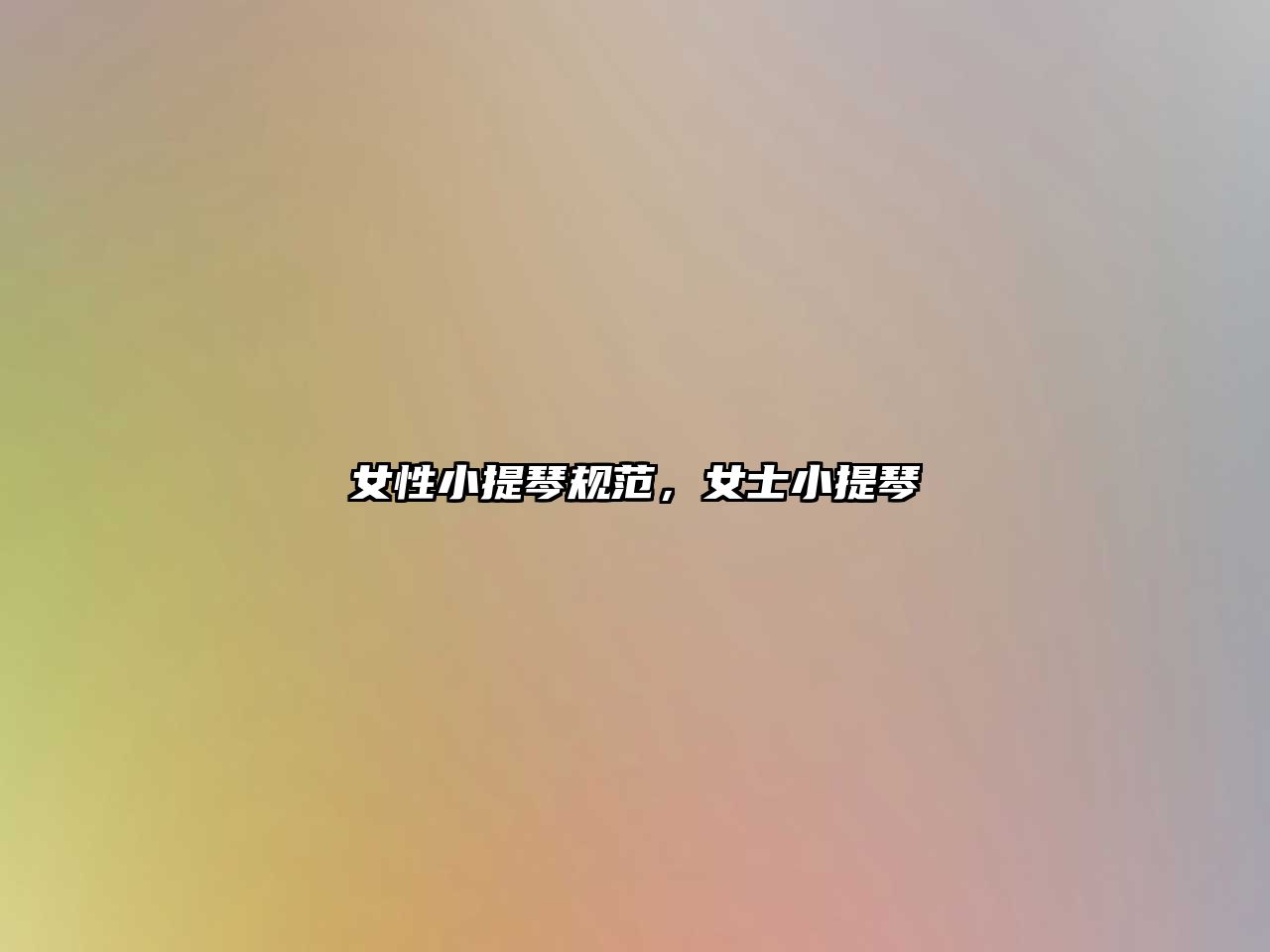薩克斯women(北美爆款《摘金奇緣》,為何中國觀眾不買賬?)
母國文化如何影響亞裔?
“缺席的父親”,與浮出地表的女性
電影中有個現象值得注意,即出現的三個家庭中,兩位主角家庭里的父親都不在。女主角朱瑞秋的父親去世
(后來我們知道故事并非如此,但“父親”始終未出現)
,而男主角尼克的父親則因生意在外,缺席了整部電影。第三個家庭,即瑞秋朋友的父親高先生,則以一個無足輕重的喜劇人物形象出現。這一看似無意的故事設計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簡單,因為“缺席的父親”幾乎是近代中國
(擴大些的話,是亞洲諸國近代都相似的歷史)
歷史中的最大象征與隱喻。

《摘金奇緣》電影劇照,圖為男主母親、男主與女主。電影講述了一個典型的灰姑娘嫁入豪門的浪漫喜劇故事:新加坡裔富豪與華裔普通移民女孩跨越階級、文化差異終成眷屬。
學者許子東在其《許子東現代文學課》中多次提及,近代五四
(甚至之前)
的諸多先賢幾乎都成長在一個“父親缺席”的家庭。這些父親不是因病或其他原因早逝,就是因吸食大煙、犯罪與軟弱而難以支撐整個家庭。于是這些男性知識分子大都由其堅韌的母親撫養,如胡適、魯迅與周作人兄弟、老舍等。這可能只是巧合,但當這個巧合與晚清中國的不堪歷史碰撞在一起,就變得意味深長:伴隨這個巧合一起衰落與死亡的是整個清帝國。
在這里,我們發現那個最古老的隱喻再次浮出水面,即父/家/國三者的緊密聯系:當它們在周代及后世儒家共同設計下成為一榮俱榮、一衰俱衰的共同體時,晚清“忽喇喇如大廈傾”的局面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趨勢。在魯迅與周作人關于他們成長的周氏大宅的回憶文章中,我們看到的難道不正是一個傳統中式家庭的衰落與死亡?而伴隨著死亡的新生,就是年輕人對父、家庭及帝國的厭倦與反抗。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女性、尤其是母親的想象從歷史的地表下浮現,成為近代中國自我構建中的重要思想資源與形象。

《許子東現代文學課》,作者:許子東,版本: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6月
在李安早期的“父親三部曲”
(《推手》、《喜宴》與《飲食男女》)
中,展現的正是“父親的退場”這個充滿悲哀與難堪的過程。在電影中,父親的退場幾乎是一種歷史必然性,他們的過去已經過去,那些曾賦予他們家國權力的制度也徹底崩潰。無論是在他們曾經成長的土地還是流落異域,這種“退場”都是不可避免的。當李安把這些故事搬到美國這一徹底陌生的環境中時,那些漸漸融入新國家與社會的子女們也在無形中“逼迫”著父親的退場。而這整個過程,都是不得不思變和展開新文化與國家建構的近代中國之轉變的延續。革命總是從“弒父”開始,五四一代青年人所面對的正是那些被看作僵化、衰朽和陳腐的父親以及他的家庭、甚至國家。

“父親三部曲”之一《推手》劇照。
這便是《摘金奇緣》這個“父親缺席”故事中華人的主要背景。作為華裔的導演朱浩偉
(母親來自臺灣,父親來自香港)
,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從這一系列想象中調動了這些資源。
著名社會學家盧蕙馨根據其在臺灣所做的田野調查寫成專著UterineFamiliesandtheWomen'sCommunity,其中她提出了一個叫“子宮家庭”
(UterineFamily)
的概念,主要指在父權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情況下,母親通過生育孩子使得他們對母親的奉獻有認同感,并且產生了一個“女人的社會”。在堅硬的男權社會與家庭中,這個被稱作“子宮家庭”的社會組織往往隱秘且不可言說,它主要作用在家庭的女性成員之間,如婆媳、母女等。

劇中男主母親,被塑造為“母憑子貴”的典型形象。由楊紫瓊扮演,放棄劍橋學業與事業發展,幫助丈夫管理家庭。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看《摘金奇緣》中的楊家甚至是瑞秋的母女小家庭,或許都可以說這是一個“子宮家庭”。在這里,作為家族——以及“子宮家庭”組織中——下一代繼承者的男性便成了組織中的核心人物。“子宮家族”通過“母以子貴”來維系和獲得一定的權力,而家族則同樣需要男性繼承人來延續。在這里我們便看到了“子宮家族”的局限,即在一定程度上它與
(男性)
家族分享著相似的目的,都得從下一代男性掌權者那里獲得其利益分紅。
而這一東方式的“傳統”模式,下意識地在影片中被延續。
西方視角的規訓與重構
健壯的男性,與個人對群體的勝利
《摘金奇緣》中出現的女性幾乎是男性角色的兩倍。值得討論的是,當這些在西方接受教育、成長和工作的亞裔男性與女性重新回到或被放置在華人家庭與國家中時,他們性別形象背后所展現的,不再僅僅是近代傳統中那些遭到貶低的東方式氣質,而是嶄新的西式兩性氣質。
男主角尼克和其好友科林·邱,他們分享著相似的男性氣質,即外形高大、五官立體、英俊、著裝得體
(時常是西裝筆挺)
,有著迷人的性感身材,性格直爽且開朗。這一男性形象在西方此類及各類型電影中比比皆是,我們可以說它是當下西方
(電影中為美國)
十分主流的男性形象。與之形成截然對比的是尼克的那些堂兄弟,他們外形大都不符合西方主流的男性形象,著裝花哨,行為放蕩。如果我們在此處加入種族和文化元素,就會發現同樣是亞裔,隨著他們不同的男性氣質所被賦予的,是不同的“形象”,甚至可以在此粗略地劃分出西方/東方這一既陳舊又新穎的二元對立。

男主尼克與女主瑞秋的對手戲中,鏡頭常將目光聚焦到尼克的身體上,而尼克的體形是典型的西式審美。
美國亞裔學者顏樂·埃斯皮里圖
(YenLeEspiritu)
在其文章《并非所有男性都生而平等:美國歷史上的亞裔男性》中指出:亞裔美國男性氣質是十分種族化的,“歷史上他們常常被描述成性無能或是縱欲過度的”。埃斯皮里圖所研究的大約是“二戰”前后的美國亞裔男性,而在尼克與科林這一代亞裔之中,美式主流男性氣質早已經融入他們的身體和觀念,使其成為這一意識形態生產和鞏固的一部分。而這也正是本片導演在潛移默化中賦予其男性主角的性別氣質。
同時,導演又不可避免地落入傳統的二元對立窠臼,再次把另一部分亞洲男性設計為“女性化”的,繼承了近代西方影視作品中對其的一貫扭曲——從形象陰森的傅滿洲,到雖然聰明睿智卻又迂腐的陳查理
(傅滿洲是英國小說家薩克斯·羅默創作的《傅滿洲》系列小說中的虛構人物。陳查理是美國小說家厄爾·比格斯筆下虛構的一位華人警探。這兩位是西方流行文化中最著名的兩大亞洲角色)
。
電影鏡頭多次流連在劇中幾位男性角色充滿健碩肌肉的身體上。勞拉·穆爾維在其著名的論文《視覺快感和敘事性電影》中指出,攝影鏡頭的凝視與窺視傾向
(scopophilia)
相關聯,是為“男性特質的”
(mascu-line)
,而銀幕上的影像狀態是受到注視觀看乃至被情欲化,是“女性特質的”。在《摘金奇緣》的多個鏡頭里,效果卻截然相反,即攝影鏡頭的窺視不但沒有“女性化”那些健壯的男性身體,反而強化了它的性感與性誘惑力
(電影中緊隨其后的情節都是與女性的性愛)
。如何理解這里的凝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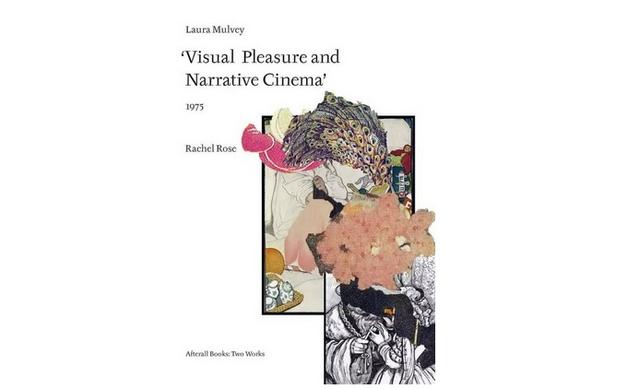
LauraMulvey:VisualPleasureandNarrativeCinema,
作者:LauraMulvey/RachelRose,版本:KOENIGBOOKS,2016年7月
在我看來,這里所折射出的,是對自我性別氣質和身份的觀看與確認。這一來自美國亞裔男性導演的鏡頭,所看到的正是上文指出的“西化”亞裔男性展現的主流男性氣質。在美國著名男性氣質研究學者邁克爾·基梅爾
(MichaelS.Kimmel)
那里,這是男性對主流氣質歸順中必不可少的過程,即在其他男性的注視下成為主流
(西式)
男性群體中的成員。
在女性這一邊,男主姐姐
(阿斯特麗德)
的故事則與近代中國女性解放產生了潛在的共鳴:她從充滿束縛的家庭
(父與夫之家)
掙脫,走出閨房成為獨立自主的女性。這一過程正是近代中國在西方思想觀念的影響下所產生的。而更重要的是,這同樣是女主角瑞秋的形象——她是“美國式的”、是“美國人”,片中人物都在不斷地指出這一點。導演此處對女性角色的設計與其對男性角色的看法存在著十分相似的邏輯:即值得稱贊的,是美式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是小家庭;而在有著傳統氣息的大家族中的女性,則必然依舊遭受著來自“家”的束縛,成為僵而不死的東方陳舊意識形態的殘留物。
在女主
(瑞秋)
與男主母親
(埃莉諾)
——這兩個代表著截然不同的國家、家庭、婚姻與女性觀念——的對峙中,最終勝利的是瑞秋。而它所暗示的,幾乎就是近代中國的命運:在強勁的西風之下,古老落后的東方獲得新生。導演雖未如此赤裸地展現這一點,但個人戰勝家族,這不正是提倡西方科學與民主的“五四”神話嗎?
雙重想象與束縛
為何亞洲觀眾反而不買賬?
這一分裂和重合再次體現了復雜性,作為美國的亞裔導演,他本身的雙重身份所造成的不同視角、文化以及由此產生和建構出的想象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動力。一方面他帶著濃重的傳統西方視角,來想象當下的東方
(新加坡與中國)
;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從自己的父母輩那里獲得了來自“母國”的一些記憶,梳理著那些在近代中國歷史中自我建構和定義中的諸多元素。
這些年輕的亞裔電影制作者借用了這一雙重建構,于是片中的女性長輩
(尼克的奶奶、母親埃莉諾以及其他七大姑八大姨)
就成為了最典型且又十分陳詞濫調的傳統中國女性形象:她們嚴肅、不茍言笑、把子女抓在手里、束縛于家族之中,一切都以家族整體利益為先,并且毫不妥協地抵抗著任何威脅……這不就是傳統男權家庭的變形嗎?尼克的奶奶就好似《紅樓夢》中的賈母,掌握著整個家族的方向,并且對于兒媳的能力始終抱著不滿和質疑。
因此,這些女性不過是男性權力的一張面目而已。性別影響在此似乎被降到了最低程度,而當她們面對來自西方的女性時,一種對于“他者”的建構則發生在東方式女性及其家族之中,即她們對美國式的個人主義所想象的是自私和對責任感的疏離。這一指責我們難道不是很熟悉?它在近代中國關于西方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批判中此起彼伏,并最終建構了東方的群體主義與西方個人主義的對立。

《摘金奇緣》中的女性核心,家族掌管者奶奶的形象。
當西方把自己當做先進、文明與諸項都高人一等的主體觀看那個被強行入侵的中國
(以及整個亞洲諸國)
時,性別總是最豐富且最具道德羞辱性的工具,于是被“侵入”的亞洲諸國都被貶低為女性,帶著長槍大炮
(男性陽具的隱喻)
的西方白人則成為無可爭議的男性化身。這一性別化導致的結果便是,亞洲大部分男性被
(西方視角)
整體女性化。
電影中,在東方式的“女性之家”中存在著一個有趣的、看似并不和諧的片段,即作為同志的奧利弗被毫無障礙地接受了,且后者毫無掩飾地展現著自己。因此這讓我們懷疑這個看似傳統保守的家庭是否真就如此?但另一方面,它或許也再次驗證了我們的分析,即近代西方對于東方家與國的女性化建構使其能夠把在傳統西方中被認為是“女性化”的同志置入其中,而不會產生任何沖突,因為其中象征著傳統男性權威的父親已經缺席。
在當下西方同志群體權益獲得一定進展的時刻,對于東方同志的想象卻依舊是陳舊的,并且與其近代對于東方的女性化想象形成新的合流。當我們覺得這一同志形象暗示著某種開放的心態時,背后被遮蔽的卻依舊是西方/東方這一頑固的想象。

劇中同志人物形象,奧利弗
這是一種種族中心式的運作模式,即它不再把那些異域文化貶抑為相對低劣的東西,而是使用那些對“他者”而言屬于正面的、崇敬的話語,并對其充滿贊賞。但即使如此,它也依舊以一種更為復雜且令人不安的方式來展現。如今那些開始被西方稱贊的“東方”,也深植于前者缺乏自省且在其文化上早已被定型的觀點之中。
在《摘金奇緣》中,我們看到一種混雜的狀態,而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創作者依舊把中國看
(seeing)
作他者,并由此產生的一系列論述。在其中建構出的鮮明的二元對立,這恰似好萊塢上世紀最典型的手段。西方人一方面想象且好奇著如今新富的亞洲人,另一方面又發現這些有著不同膚色的“他者”其實和自己分享著完全一樣的意識形態,這讓他們能夠與其產生安全且親密的共鳴。它與《了不起的蓋茨比》和《華爾街之狼》這類電影所產生的相似性,再次加強了這一觀點,即某種美國式的“夢想”。
也正是在這里,對于《摘金奇緣》這部以“全亞裔陣容”作為宣傳噱頭的電影,在西方獲得了空前熱烈的歡迎、贊賞和票房成績。但對于近代歷史中始終被觀看的“他者”——中國觀眾而言,這個熟悉的形象與故事所激活的是更為復雜的歷史記憶。華人曾作為強勢西方目光的接受者,它被塑造與建構的形象往往都帶著強烈的屈辱印記,這是我們希望拋棄的。而對于那些亞裔移民在美國所遭遇的種種問題與困境,卻又是我們一無所知的。在這一雙重情緒下,隨之而來的是對他人想象的反感以及某種強烈的隔閡——這或許就是為什么《摘金奇緣》在國內遇冷的原因。
這種雙重的困境與束縛,是近代西方對中國那籠統且粗線條的想象難以描述的。反映在這部“外黃內白”的電影中時,它們便成為某種大雜燴般的含混不清。在我們的閱讀與觀影記憶中,似乎還沒有哪一部作品能夠恰如其分地處理這些復雜性——這或許正是我們可以期待與開墾的方向。
作者:重木
編輯:走走,寇淮禹;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