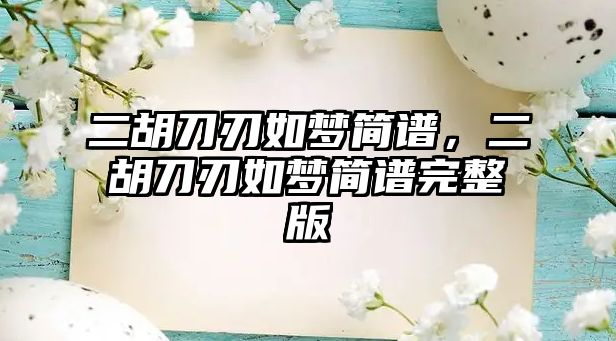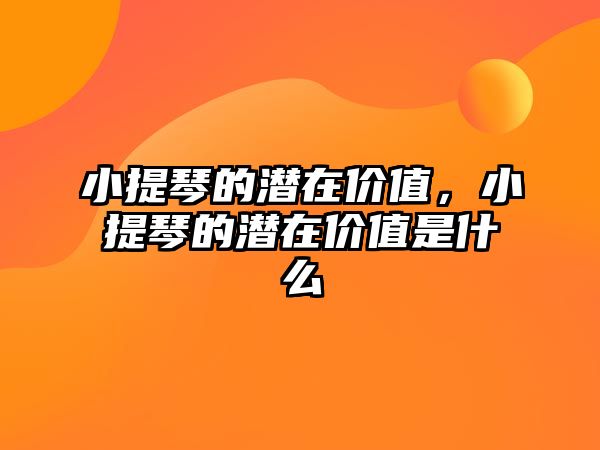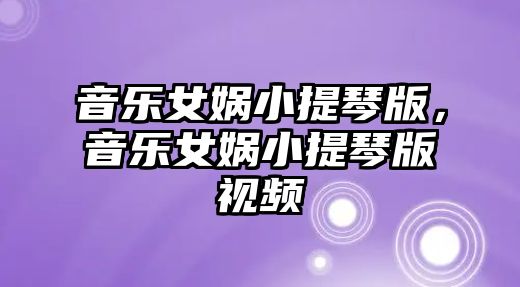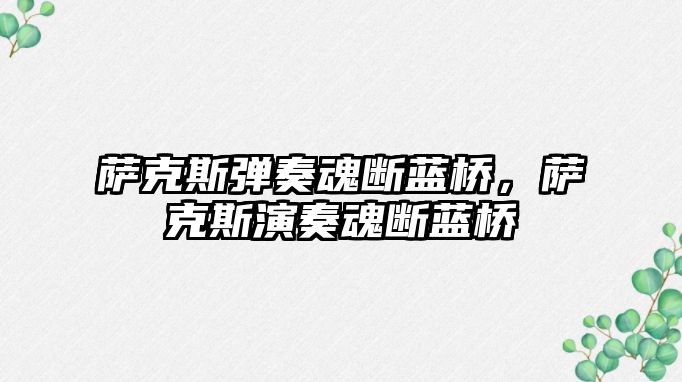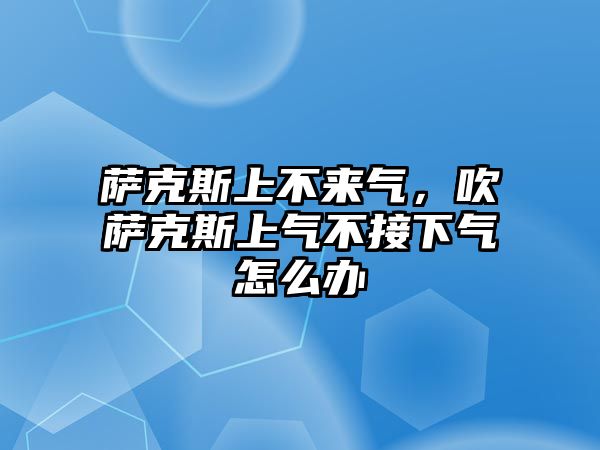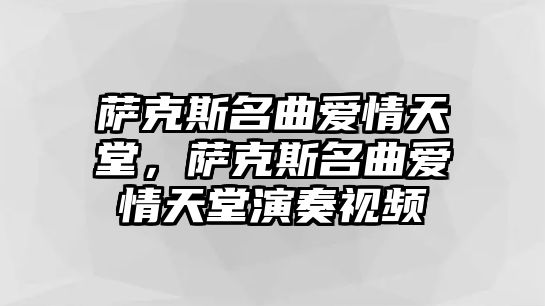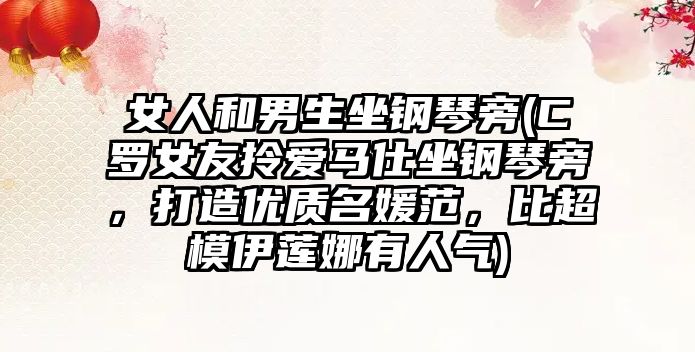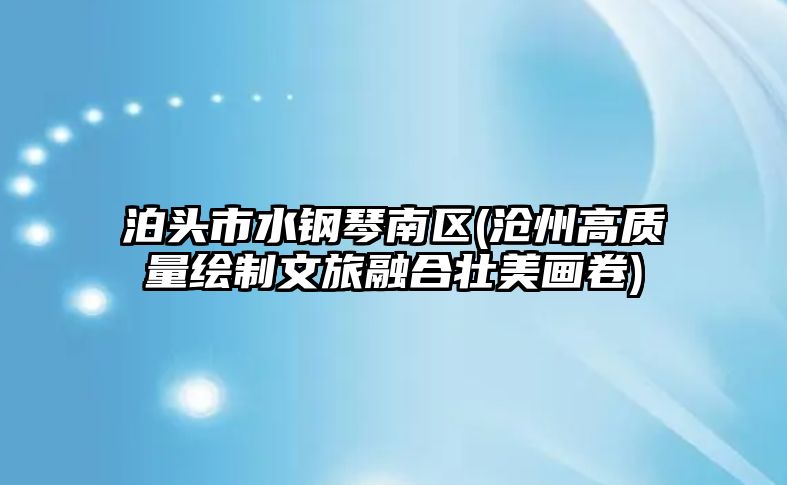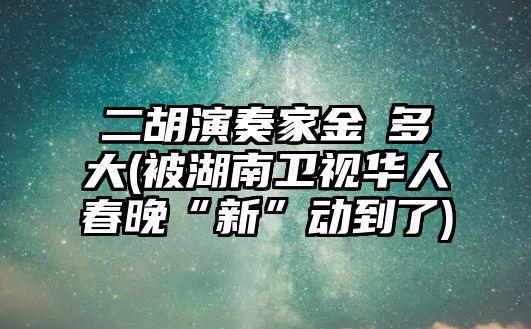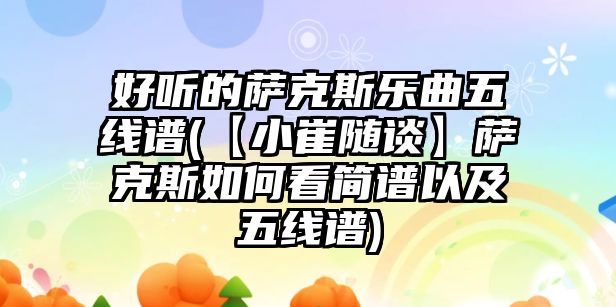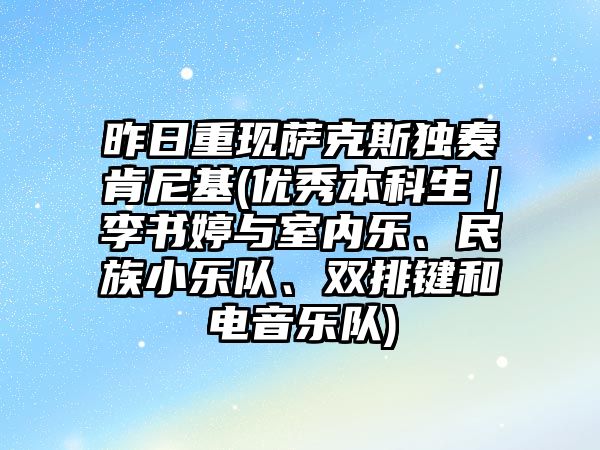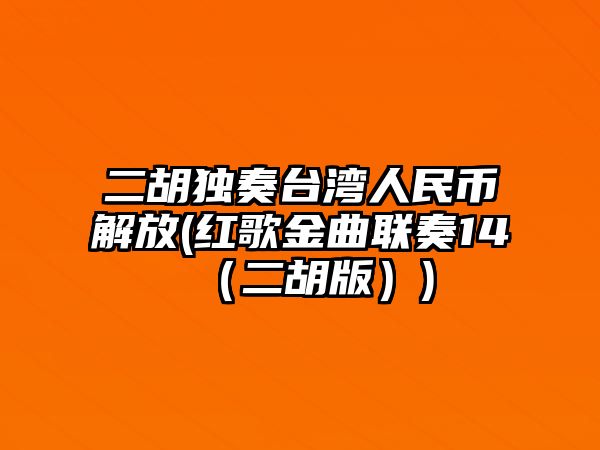二胡底座叫什么(街頭音樂家、乞丐與二胡)
-
 樂器資訊網(wǎng)
樂器資訊網(wǎng)
- 二胡
-
 2024-07-20 01:36:18
2024-07-20 01:36:18 - 瀏覽量:840

中國人認(rèn)為美國的街頭音樂家是乞丐。
美國人認(rèn)為中國的乞丐是街頭音樂家。
適讀上海音樂學(xué)院洛秦教授的《走進(jìn)美國街頭音樂》一文,感慨于美國的音樂家,中國的乞丐。
到美國去,去感受他們那兒的音樂氛圍。洛秦教授曾兩度驅(qū)車從西雅圖往東橫穿美國,采訪了若干活躍于美國各城市的街頭音樂家:那個(gè)在華盛頓大學(xué)大學(xué)街上演奏的黑人老樂手、那個(gè)拒絕給他拍照的黑人吉它手、那用小提琴演奏蘇格蘭民歌的兄妹三人、那個(gè)拉“克萊斯勒練習(xí)曲”的華盛頓大學(xué)音樂學(xué)學(xué)院小提琴專業(yè)的學(xué)生潔絲卡、還有那個(gè)為了演奏與歌唱放棄工作的彼特……這些音樂人走上街頭,并不完全為了錢,他們有著良好的音樂素養(yǎng),對(duì)音樂有著自己獨(dú)特的詮釋,他們有走上街頭很人性的理由,這些理由中閃爍著陽光般的真誠,他們?yōu)榱税岩魳穾У浇诸^,把信仰融入音樂。
我感動(dòng)于美國的音樂家,然而比照中國,卻少有街頭音樂家,有的僅是那些拉著所謂的二胡在街頭討食的人們,他們的二胡拉得大多不堪入耳,我曾經(jīng)和一個(gè)這樣的老者攀談過,他告訴我他小的時(shí)候因故瞎了雙眼,早些年還可以過活,現(xiàn)在不得已和一個(gè)乞討的同伴一起走上街頭,以前根本不會(huì)拉二胡,現(xiàn)在沒辦法才勉強(qiáng)試著拉一些自己熟悉的小調(diào),只認(rèn)為這樣會(huì)比徒手乞討效益稍微好一點(diǎn)。他拉的二胡確實(shí)不成什么曲調(diào),二胡在手中僅僅是一個(gè)乞食的工具。
在中國,我們會(huì)遇到很多這樣乞食的人,他們手中的樂器不約而同的都是一把破舊的二胡。這其實(shí)很讓二胡尷尬,中國的民族樂器很多,大多都流傳于民間,但乞食者為何偏偏和二胡結(jié)緣?思索良久,也許是瞎子阿炳的《二泉印月》太出名了,于是他的形像就成了國人心中的范式,他的二胡曲就成了悲傷哀憐的代名詞。以致于多少年過去了,二胡在人心中依然是一種地位低俗的樂器;以致于一提到二胡,就讓人們想起《二泉印月》,相起它的傷痛、苦楚。雖然劉天華先生對(duì)二胡的升華作了莫大的貢獻(xiàn),把它從民族器樂伴奏的大家庭中獨(dú)立出來并第一次在演奏上借鑒西方小提琴的拉法,然后又第一次把它納入音樂學(xué)院的殿堂,但阿炳卻以他獨(dú)特的形像與《二泉印月》讓二胡實(shí)實(shí)在在的留在了苦難的民間。幾十年過去了,演奏二胡的人可謂越來越多,但二胡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并沒有什么實(shí)質(zhì)性的變化,我學(xué)二胡的這幾年,總是在新朋友的疑惑與不解中度過:“為什么會(huì)選擇這樣一種樂器呢?”我無言以對(duì),需要解釋些什么呢?二胡確實(shí)沒有鋼琴的華貴,沒有小提琴的鮮艷,但也并不表明就注定要與傷痛與哀憐聯(lián)系在一起。可悲的是,現(xiàn)在有很多的影視節(jié)目無形中正在宣傳這一主題,一當(dāng)遇到凄楚、苦痛,烘托哀憐的主題時(shí),二胡就出來了。記得《武林外傳》里,小六演奏的那支悲哀曲子,用的正是二胡,悲哀與乞討成了二胡的兩個(gè)主題。
二胡與小提琴是中西兩種最主要的拉弦樂器,有很多近似的特性,但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卻是天上地下,我想:人們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更多的可能取決于二者的外形。
二胡生來就和坐相關(guān),只有坐著拉才能最好的施展演奏者的技能,而小提琴則不然,站坐皆可,而且站起來似乎更能靈活自如,更富有表演性,也更有觀賞性。對(duì)于表演藝術(shù)來說,站當(dāng)然會(huì)比坐好得多。近年來新一代的二胡演奏者雖也改用站著拉二胡,但總覺得不倫不類,二胡底座失去了依托,搖搖晃晃,實(shí)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技藝的發(fā)揮,只是在追求一種視覺上的感官效果。
二胡的顏色大多是深褐色的,這也比不得小提琴的紅色,暖色調(diào)和冷色調(diào)給觀眾帶來的心理感覺是不一樣的。
二胡的音色和小提琴就更是完全不同,二胡皮箱發(fā)音,音色低沉,如泣如訴,小提琴木箱發(fā)音,音色高亢明亮,振奮人心。小提琴就好比天朗氣清,而二胡是柔美纏綿。
雖然在實(shí)際的演奏當(dāng)中,二胡并不比小提琴差;雖然在當(dāng)代二胡曲中,喜慶熱烈的樂曲遠(yuǎn)遠(yuǎn)多于悲傷哀憐的樂曲;雖然二胡音色類似于人聲,更多的帶有歌唱性,但也許是人們根深蒂固的“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觀念在作怪,二胡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仍然沒有改觀,好在現(xiàn)在學(xué)習(xí)二胡的人越來越多,學(xué)習(xí)者的年齡越來越小,各地區(qū)的二胡協(xié)會(huì)(學(xué)會(huì))也相繼成立……相信我們的二胡,相信我們的民樂,相信在世界樂壇上它也能與小提琴并駕齊肩。
突然想起那一天在街邊上拉著二胡的那個(gè)老者,那是一種心神自醉的感覺,雖然他的技術(shù)并不如何,但他顯然已步入了一個(gè)他自己營(yíng)造的境界,用心在拉著琴,用心在感染著路人。這激起了我久違的興奮,因?yàn)橹皇撬哪欠N沉靜,就足以讓我認(rèn)為:我們中國的街頭,除了乞丐,也有音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