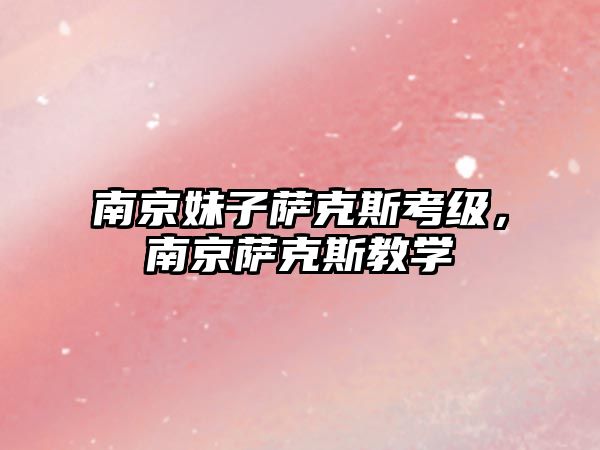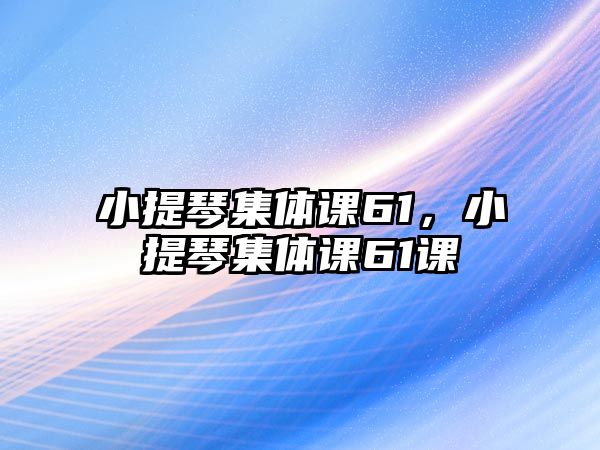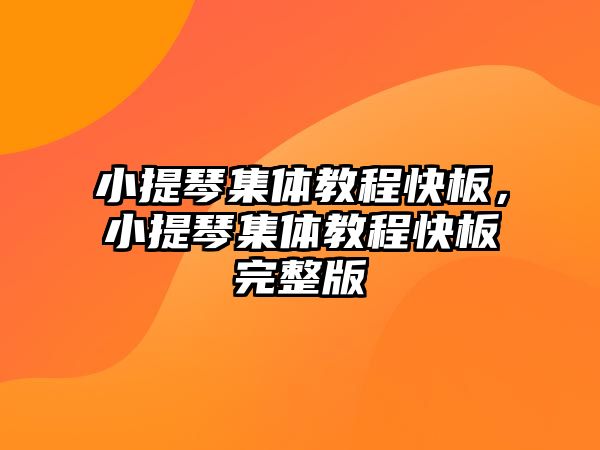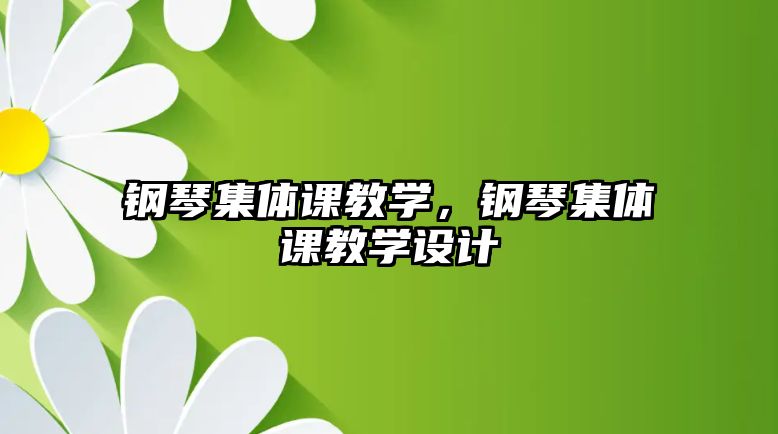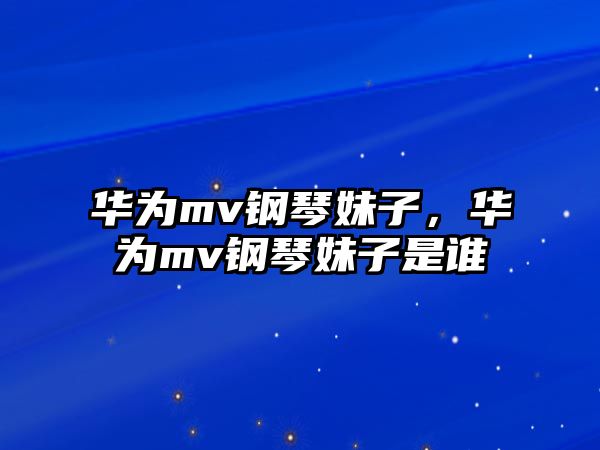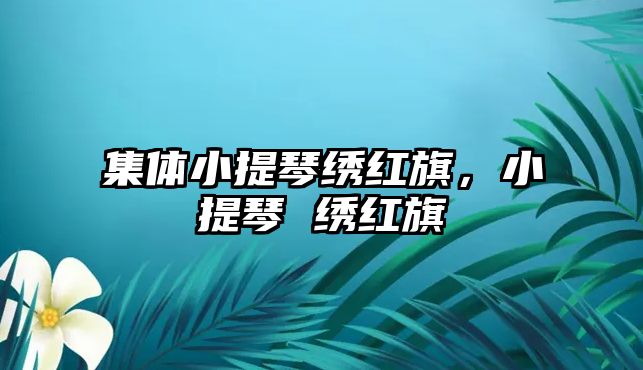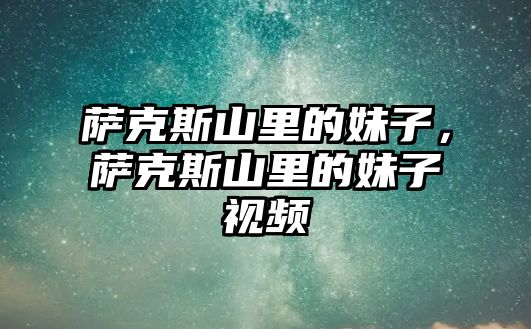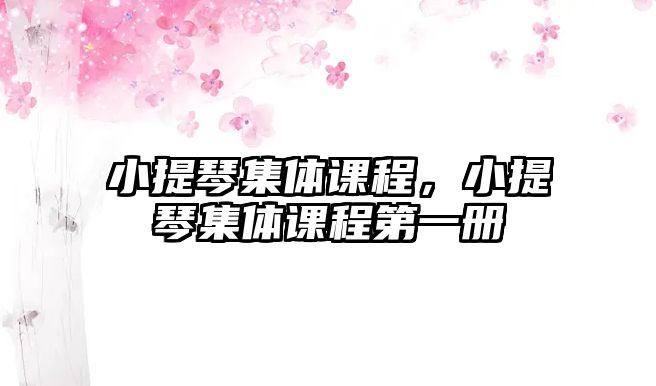怎么用二胡演奏花鼓戲(花鼓戲《打銅鑼》《補(bǔ)鍋》覺醒人心)
-
 樂器資訊網(wǎng)
樂器資訊網(wǎng)
- 二胡
-
 2024-04-04 19:43:16
2024-04-04 19:43:16 - 瀏覽量:43
譚圣林
“收割季節(jié),谷粒如金。各家各戶,雞鴨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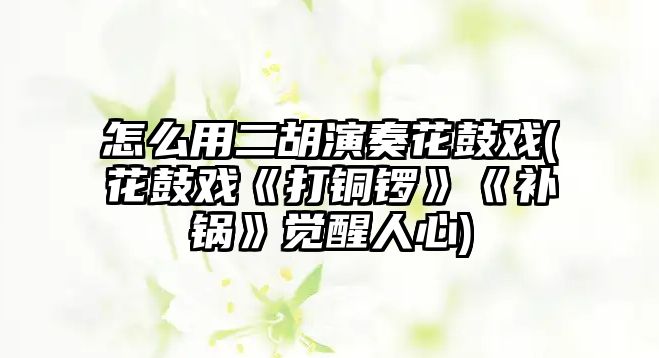
上個世紀(jì)七十年代初的農(nóng)村老家,生產(chǎn)隊(duì)大集體每天按時出工,就像如今城里朝九晚五上班一樣,隨著胡隊(duì)長一聲哨響,斗笠扁擔(dān)籮筐鏟子犁耙立馬分布在田間地頭,種豆的種豆,犁田的犁田,挑糞的挑糞,既是勞有所長的分工協(xié)作,又有彼此關(guān)系的親疏搭配。
與此同時,山坳上電線桿的高音喇叭也如約響起,每次開鑼的是花鼓戲《打銅鑼》,蔡九哥爽朗的高腔,林十娘潑辣的刺味,二胡嗩吶鑼鼓有序穿插奏響的韻味,幾乎天天撒遍田野,喊醒泥鰍鱔魚,覆蓋鳥語花香。
第二個節(jié)目雷打不動的是花鼓戲《補(bǔ)鍋》。
“(女)風(fēng)箱拉得響,(男)火爐燒得旺。(女)我把風(fēng)箱拉,(男)我把鍋來補(bǔ)。(女)拉呀拉呀,(男)補(bǔ)呀補(bǔ),(女)拉呀拉呀,(男)補(bǔ)呀補(bǔ)。(男)幫助我的丈母娘,蘭英我的同志妹嘞。(女)幫助我的媽媽娘,小聰我的同志哥嘞。”農(nóng)家女青年蘭英與挑著行頭走村串戶的補(bǔ)鍋男青年李小聰自由戀愛,但是遭到勢利眼媽媽劉大娘反對,就著修補(bǔ)煮豬潲的大鐵鍋這檔家常事,兩位年輕人一唱一和,成功說服大媽,故事簡單,情節(jié)自然,唱詞通俗,百聽百味,高潮處時常令人忍俊不禁。
那時的人腦子單純,都是一根筋,信息也單一,日復(fù)一日干活記工分,雖然累得像狗,腹中空癟,但也還是圖個快活。花鼓戲一上口,渾身是狠勁,一個個就像打了雞血加了催化劑,腳踩打谷機(jī),“唔唔唔”響徹云霄,口里也跟著吆喝“蔡九哥林十娘”。
中午聚在小河邊柳樹蔸下歇腳吃鹽粥時,年紀(jì)大的男人抽煙牛飲山泉,小伙子則按捺不住想當(dāng)李小聰,用采摘的一串茶苞或者捉到的一只野兔子,趁機(jī)去拉扯長辮子“蘭英”和未來的厲害岳母娘。
《打銅鑼》敲鑼長鳴,彰顯的主題是要保護(hù)集體每一粒谷,不能私挖集體的墻腳,偷占集體的便宜,損公肥私害人害己。
《補(bǔ)鍋》以鍋為媒,強(qiáng)調(diào)革命工作是整體,七十二行都要緊,職業(yè)沒有尊卑貴賤之分,打鐵織布磨剪子,砌墻燒炭筆桿子,每一位正當(dāng)勞動者都了不起。
戲唱數(shù)遍,入腦入心,其潛移默化的教育引導(dǎo)作用,也如山間瞄準(zhǔn)趨勢追求正直的春筍一樣挺立出來。
為了保證過年過節(jié)每家能分得到豬肉,生產(chǎn)隊(duì)在遠(yuǎn)離大屋場的坳腳下建了個養(yǎng)豬場。夜幕降臨,萬籟俱寂,豬鼾聲此起彼伏,但是豬場后面連排的墳冢,陰森逼人,有事串門的寧可繞遠(yuǎn)道,也不敢輕易往豬場方向經(jīng)過。蹊蹺的是,豬場居然在一個暴雨夜晚被盜,木窗戶的七根檁條齊刷刷被砸斷,豬場倉庫里一擔(dān)米頭子(米與糠混合一起)不翼而飛。偷吃豬食,可見家里是揭不開鍋了,不然低頭不見抬頭見,誰愿意背負(fù)一個被眾人喊作賊古精的罵名。
其實(shí)大家心知肚明,十有八九是豬場飼養(yǎng)員老斗古順走了,為了掩人耳目故意砸窗鼓搗出被盜的假象。他屋里兩公婆帶著6個崽女和兩個老人,吃起飯來,鬼搶齋樣的,一人一碗就要10碗,實(shí)在不夠了,就用米湯和洗鍋水煮著南瓜藤和紅薯葉湊合著下咽。最近正值青黃不接之時,饑不擇食,肚皮難受哪還顧得上臉皮難堪,只得損公濟(jì)私,做出見不得光的糗事。不過誰也拿不出鐵證,誰也不敢當(dāng)面戳穿。
秋收歸倉后,隊(duì)上在集體曬谷坪里上演了一場花鼓戲,劇情原原本本模仿《打銅鑼》,為了演得像模像樣,扮演蔡九哥的安壇子和扮演林十娘的毛妹子,還步行七八里路,找到縣花鼓劇團(tuán),學(xué)習(xí)長沙方言發(fā)音,練習(xí)提氣沉氣唱潤腔。相鄰隊(duì)上戲班子里吹嗩吶的龍眼子阿張子也來捧場,隨著鑼鼓大小鈸加花帶水響起,一臺教育社員雞鴨不能偷吃集體谷子損害集體利益的大戲閃亮登場,現(xiàn)身說法,覺醒人心。
那場花鼓戲演完之后,豬場里一擔(dān)米頭子奇跡般回來了,木窗戶上的檁條也修復(fù)一新。這次,大家伙不再說三道四深究是誰弄的這一出“夜戲”了。只是茶余飯后,扯起牛喉嚨哼唱花鼓戲的多了,雖說字不正腔不圓,卻是拽味得很。
我們那是正在上小學(xué),放學(xué)路上,也有好事者搞面小銅鑼,打打唱唱,遇見誰家雞鴨下田吃谷,眾人立即充當(dāng)“蔡九哥”合圍驅(qū)趕。
至于隊(duì)上的篾匠師傅貓格里,與羅娭毑的女兒雪妹子糾結(jié)兩年的戀情,也開始由陰轉(zhuǎn)晴。貓格里是外來做小手藝的,在羅娭毑家破竹削篾,編織箢箕簸箕,與大眼膚白的雪妹子來回擦肩對上了眼神。但是老兩口一直虎著臉反對,認(rèn)為女兒生相如西施,怎么能與一個手粗腳糙的外來小篾匠過一世,貓格里這丑名聽著就別扭,至少要嫁個開著拖拉機(jī)呼呼生風(fēng)的后生子吧。
趁著上屋場老牛屋里娶媳婦,搭起舞臺唱花鼓戲《補(bǔ)鍋》,貓格里雪妹子以主家派發(fā)喜煙喜糖為誘惑,拖著羅娭毑看戲入戲,讓臺上生火補(bǔ)鍋照亮臉龐的“李小聰和蘭英”與羅娭毑互動:“跑馬莫怕山,行船莫怕灘。幫助我那丈母娘(媽媽娘),改造那個舊思想哪。”
貓格里祖輩以竹編為生,他不遠(yuǎn)幾百里來到此地,看中了漫山遍野的翠竹筍林,他當(dāng)然不甘于游走鄉(xiāng)間,吃百家飯編幾擔(dān)籮筐。隨著惠民富民政策落地,他用早些年的積蓄作頭本,開辦了一家貓人竹編廠,成了竹編技藝傳承人,出品竹席竹椅竹枕竹杯竹墊,甚至出爐了城里人的寵物用品狗窩、鳥窩、貓窩、兔窩、倉鼠窩。
一技在手,吃穿不愁。羅娭毑心服口服。貓格里雪妹子終成眷屬。婚禮大成,戲班子二胡笛子交錯調(diào)和,聲振林木,激情演奏了一輪花鼓戲《補(bǔ)鍋》曲調(diào)。
堅定地維護(hù)每一份集體利益,公正地尊重每一個社會職業(yè)。雖然生活環(huán)境生產(chǎn)方式完全變了,但花鼓戲《打銅鑼》《補(bǔ)鍋》唱出的主旋律,依然是時代倡導(dǎo)的好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