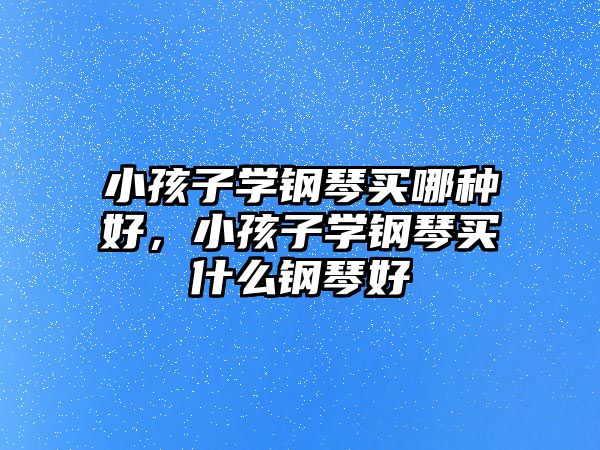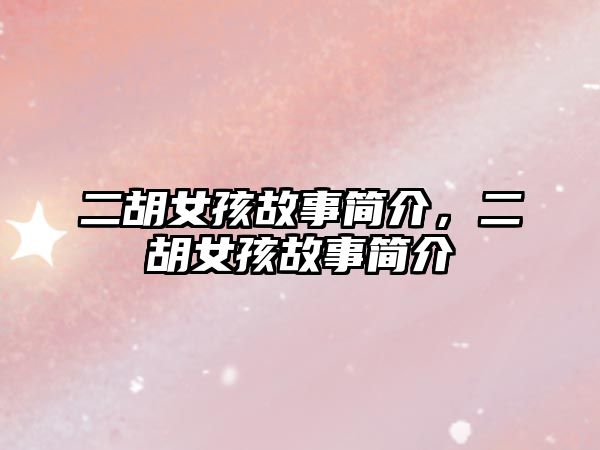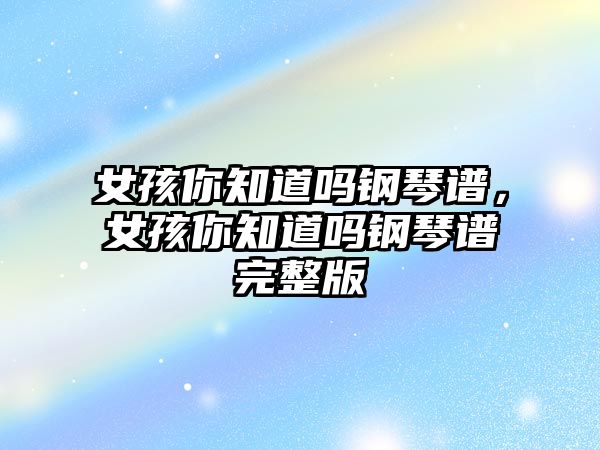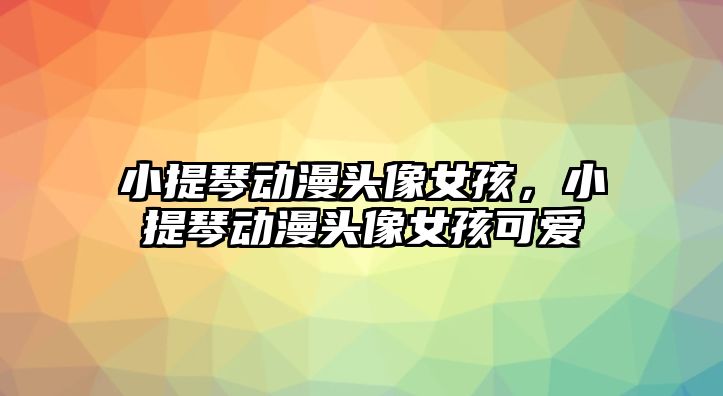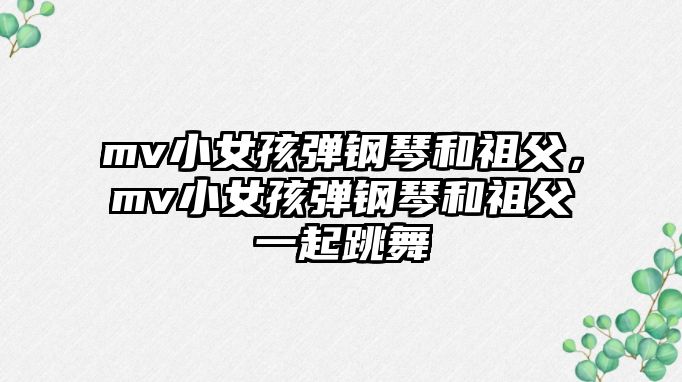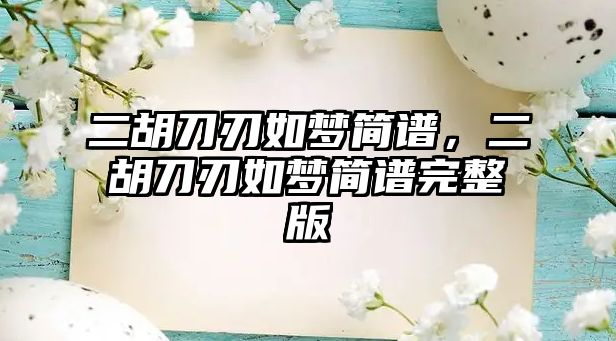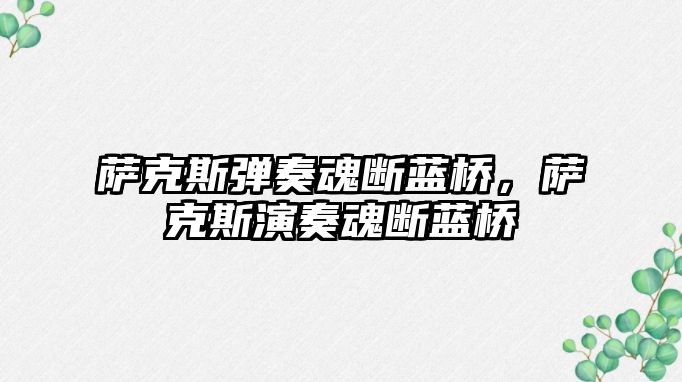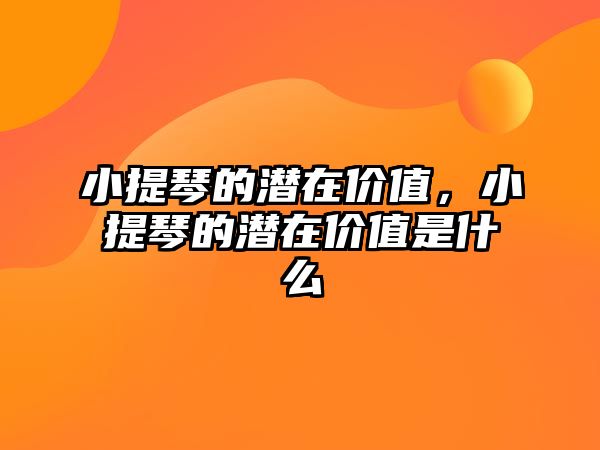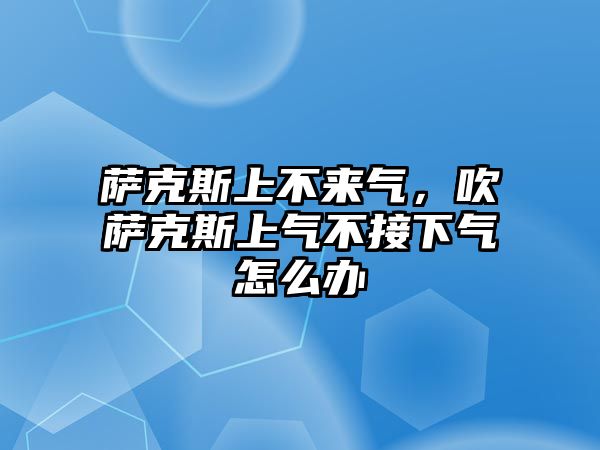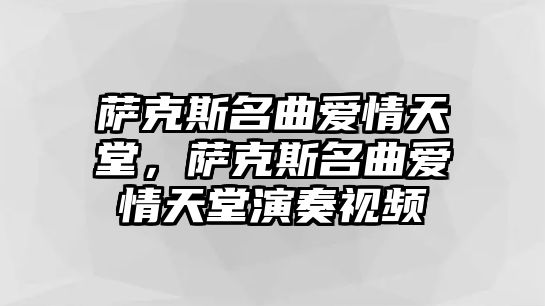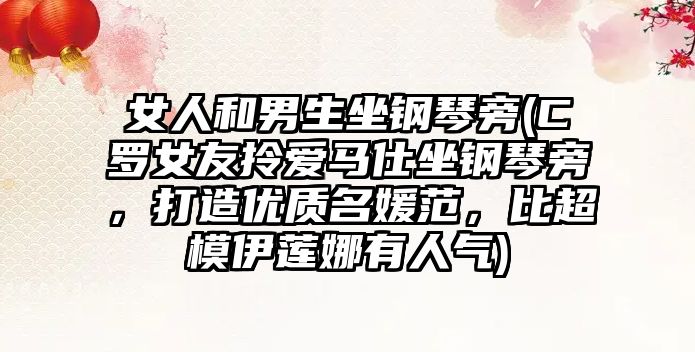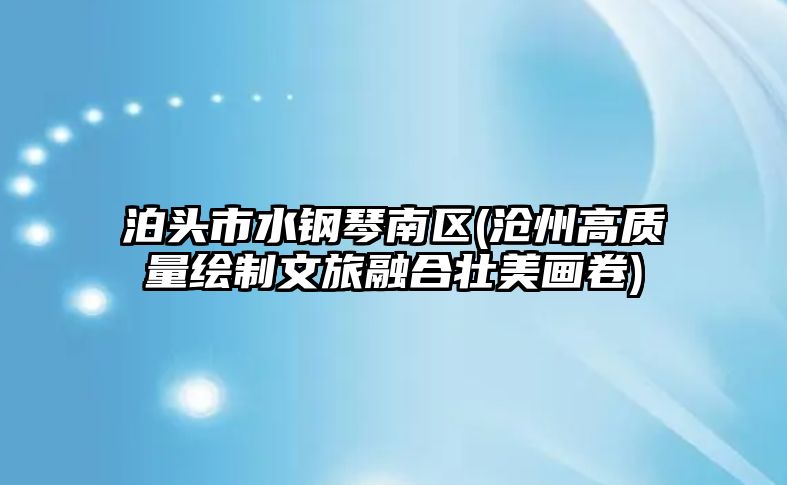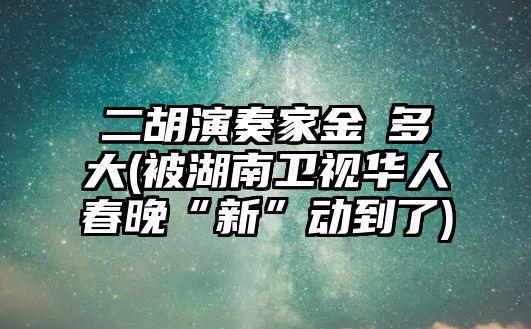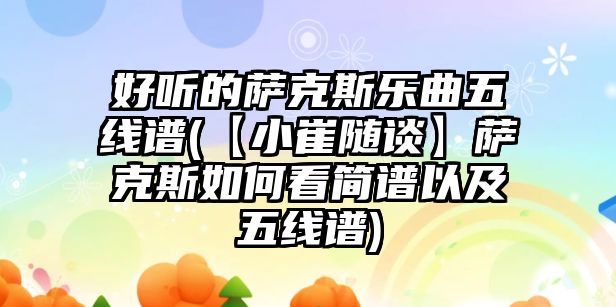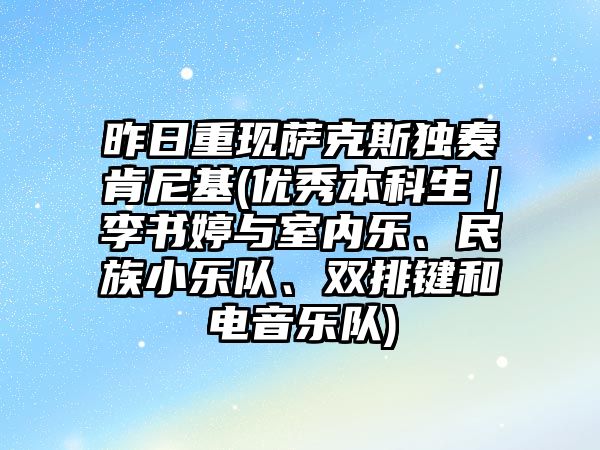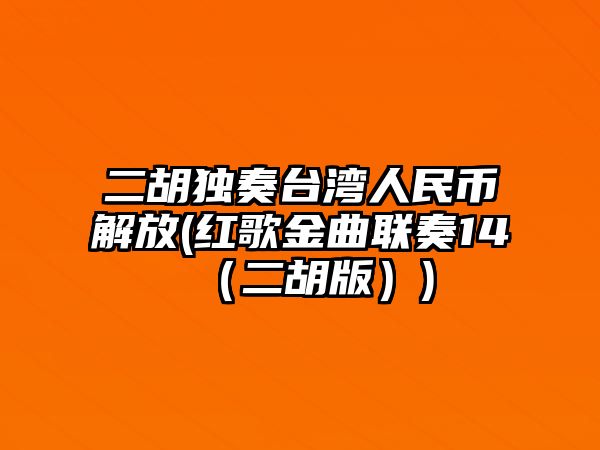二胡獨奏賽馬小姑娘唱段(拉二胡的小女孩)
文/戚利
碰見她,純屬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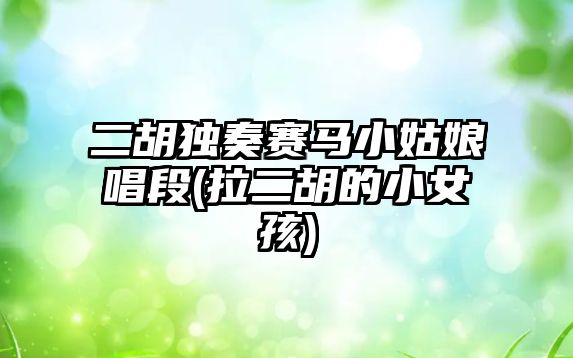
自從天氣轉暖,我就喜歡上了暴走。晚飯后,從家里出發,沿著歷山路北行,到花園路左拐西行,穿小明湖公園,經西門,上泉城路,沖東方向直道下來,全程約需2個小時。走個汗涔涔,好不愜意。
暴走的原因有兩個:一來感覺人到中年,似乎該學著養生健身,去去一身贅肉;二來年關時曾在岳父面前夸下海口,發誓要減到80公斤以下。話好說,事難做,沒有行動,總感覺過意不去,畢竟這一身肥肉不會平白無故地消失。不過真走起來,還上了癮。
濟南充其量是個二線城市,11點以后大街上就幾乎杳無人跡了。不過,八九點鐘,正是朝陽時段,剛吃過飯的中年兩口,在家休閑的老人,逛商場的年輕的學生,推著嬰兒車散步的年輕一家人,滿滿當當地擠到步行一條街上,街道兩邊的商場都大開著門,冷氣嗖嗖地從大廳里直躥到路面上,門口的大喇叭播放著各種誘人的促銷廣告。馬路上的燈似乎也比其他街道更亮一些,白咧咧地照著被太陽的熱曬透了的青石板,歸家的車鳴著喇叭,迅疾地從路中央駛過,讓人聯想到四十年代的夜上海生活。
碰見她時,我剛從三聯家電拐進泉城路。迎面擦肩而過的陌生人一個接一個,在紛紛攘攘的城市噪音里,突然我的耳邊隱隱約約傳來一種極盡熟悉的聲音,如沙漠長途跋涉的旅者偶遇一線清亮的溪水,不太真切,卻極具誘惑力,瞬間頓住了我前行的腳步。
我停身,凝神,屏息。是的,我聽到了,雖然時有時無,時強時弱,但這次是真真切切的——二胡!因為兒子學的樂器就是二胡,五音不全的我幾乎跟著兒子聽完了他所能彈奏的所有曲目,琴弦與弓子之間摩擦產生的那種獨特的音質還是被我馬上從嘈雜中辨識了出來。
沃爾瑪廣場大招牌下的兩面磚墻投射出一片陰影,一個小女孩就坐在陰影里。顯然凳子太矮,用來拉琴并不合適。女孩坐下去,一把胡琴立起來,比她的頭還高。女孩穿著短褲,白上衣有些長,琴筒就埋在衣服的褶皺里,根本就不像個正兒八經拉琴的。小女孩約莫八九歲模樣,看穿戴并不落魄,且是獨自一人,打眼一看,就知道她和平日里那些身患殘疾的賣藝人是有區別的。
小女孩的琴技并不高超,運弓子的手端不平穩,忽上忽下,忽前忽后,琴聲吱吱呀呀,勉強能聽出個音來,看起來她是在拉,卻更像是在玩。盡管也能湊合著拉出一些曲調來,但是無論是從音準上來看,還是從節奏上來看,都表明她只是一個初學者。我甚至還從琴弦干澀無力的聲音里,聽出了她連松香都沒有打好。
生活總是充滿謎團。一個很小的會拉二胡的女孩,夜晚獨自一個人坐在繁弦急管的城市街道邊,為了什么?我把注意力更加投注到女孩身邊,才發現,就在女孩的前面,有一個大敞口的精致的工藝小手提箱!陰影里,不仔細看還真是難以發現,我不禁啞然失笑。
我的第一個意識就是馬上掏出手機,對準角落里的小女孩,準備拍一張,拿回家給兒子看看,希望對似乎已經放棄了每天練琴的他有所觸動。第一張照完了,效果并不理想,畫面太暗。興許是第一次出來有些羞澀(因為我實在沒有看出來小女孩是真心地投入進曲子里),小女孩一直在埋頭拉著二胡,我的舉動并沒有引起她的注意。
我打開閃光燈,照第二張像。隨著咔嚓一聲,強烈的閃光顯然嚇著孩子了,她驚恐地抬起頭,望向我,二胡的弦音也就此戛然停住。面對她投向我的目光,我有些尷尬,急忙將手伸進口袋,摸索了一會,才記起里面共三百五拾元整,沒有更小額的錢。手揣在口袋里,捏著那張五十的,我為難了。
這么小的孩子,要是給她這么多錢最終是會交到家長手里的,對她沒用。況且,如果就這么容易讓她得到意料之外的高額的錢,對孩子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我繼而想到了孩子的父母,我斷定她的父母一定就在附近,說不定此刻正在默默地注視著眼前發生的一切呢——冬初一寒假去火車站當志愿者的時候,我和其他孩子的家長就是這么做的。當然,我要是靠近了與孩子進行對話可能更不合適。
我抬頭環顧了一下四周,不遠處有一個流動的兜售飲料的便車,我急忙跑過去,將五十元遞上去:“來一瓶果粒橙。”,售貨的大姐看了看我,臉上有些不大高興,我歉意地朝她笑笑。拿著找回來的錢就往回走——小女孩依舊在埋頭拉二胡,曲目是《賽馬》。
我靠近她,將五元錢扔進她面前的箱子里,我竟然吃驚地發現里面早已經零零散散地放了很多錢,不過五元已經是里面最大額的了。小女孩并不在意是否有人會往箱子里扔錢,所以我沒有聽到感謝聲,她正放了弓子,拿手撥弦,模擬著《賽馬》中得得的馬蹄聲。
為了不影響孩子繼續表演,扔下錢,我就急匆匆地趕路了。
反正時間有的是,邊走邊琢磨,也許女孩的父母是想讓孩子出來鍛煉一下膽量?抑或是想通過這樣一種方式督促孩子練琴,更可能是希望讓孩子看到藝術的魅力。不過,偶爾這樣做做倒說得過去,長此以往,孩子很容易把藝術和銅臭聯系到一起,那就得不償失了。
我就又為小女孩的未來擔心起來,真想找到她的父母,對他們說:請你們一定要告訴孩子,所有那些給錢的叔叔阿姨是希望用這種方式鼓勵她的勇敢、支持她的選擇,千萬別把藝術俗化了,害了孩子。想著想著又笑起自己,最近到底怎么了?多愁善感的,無他,還是先走自己的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