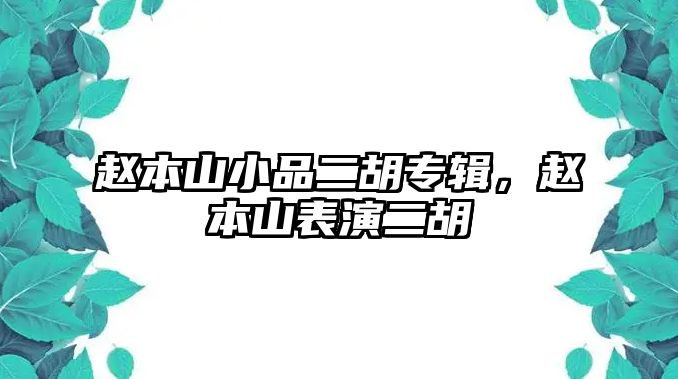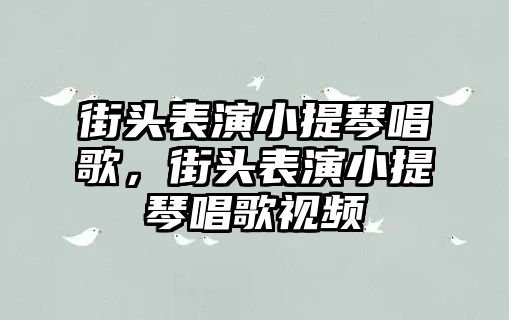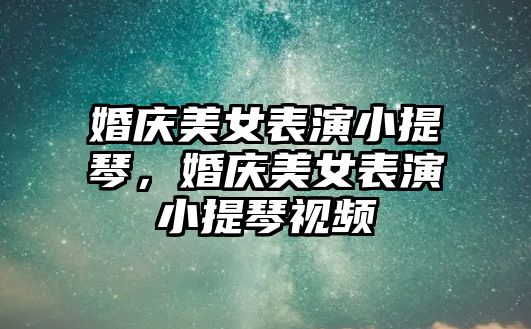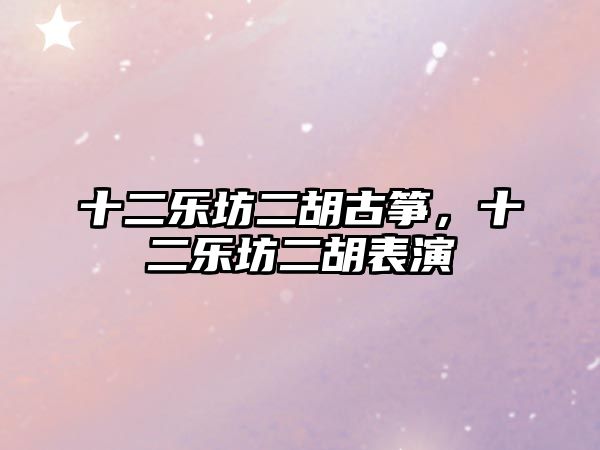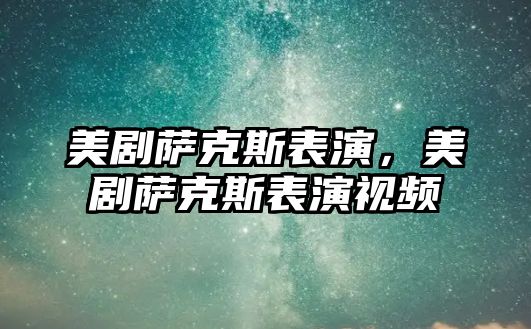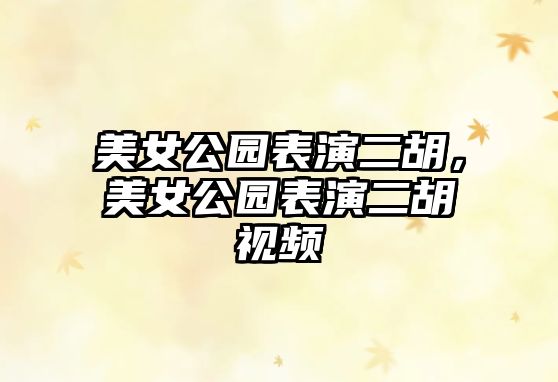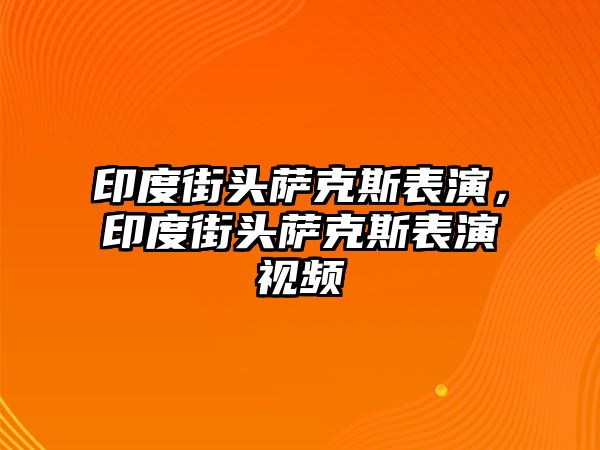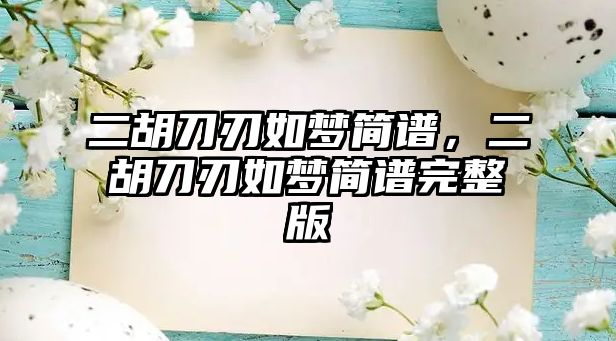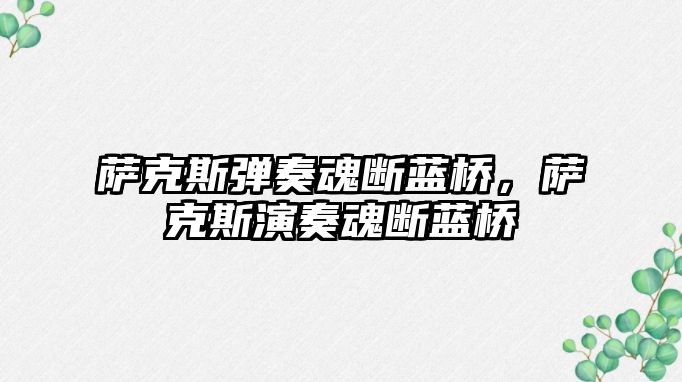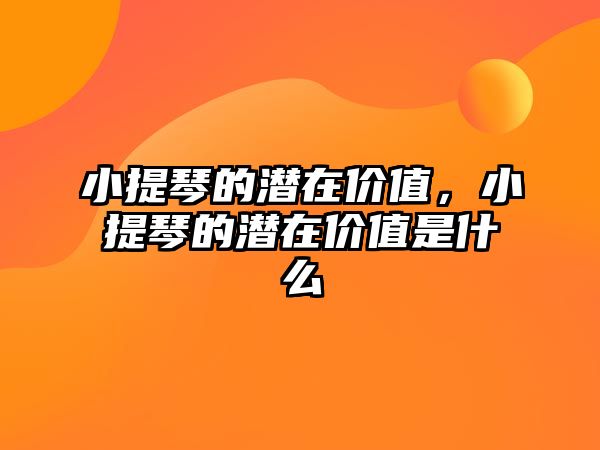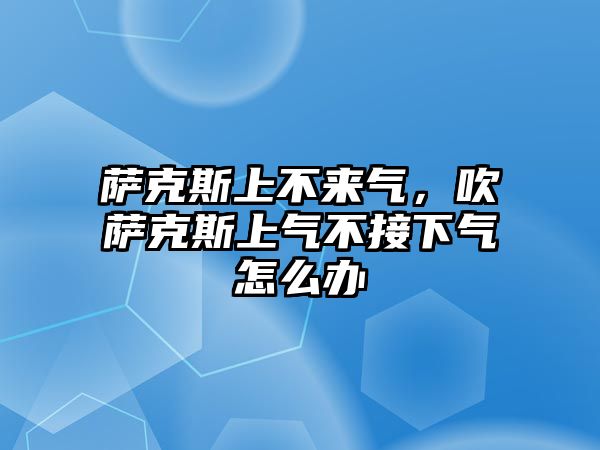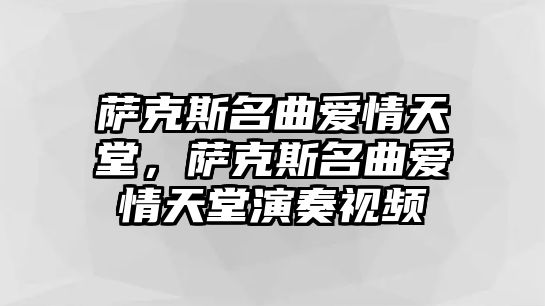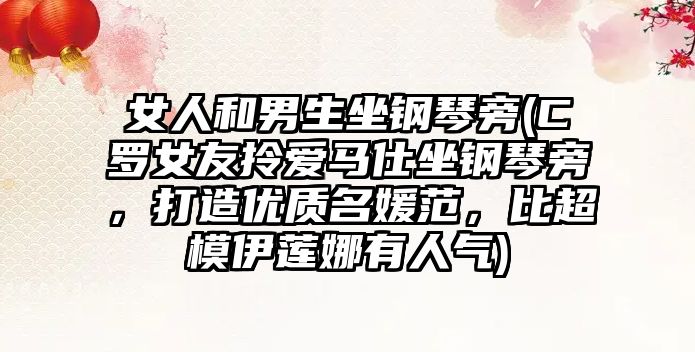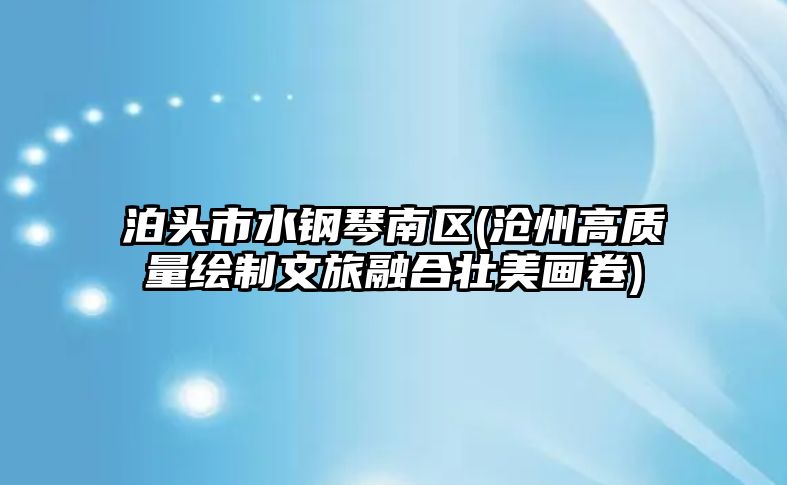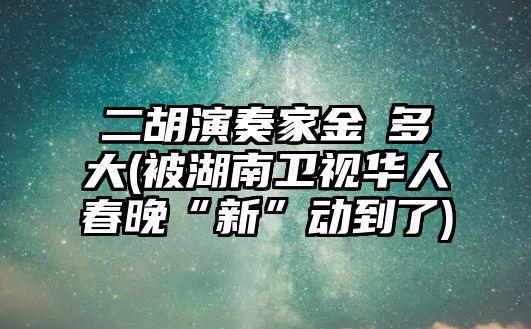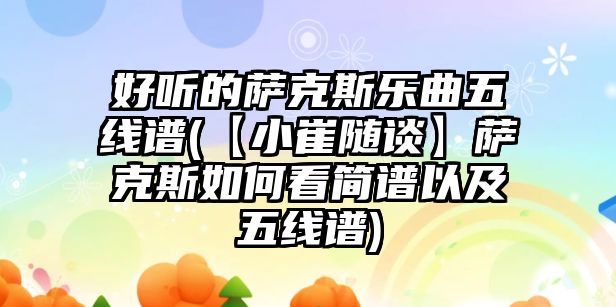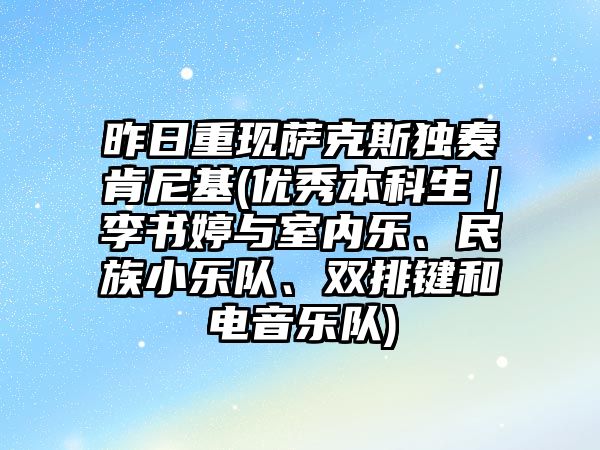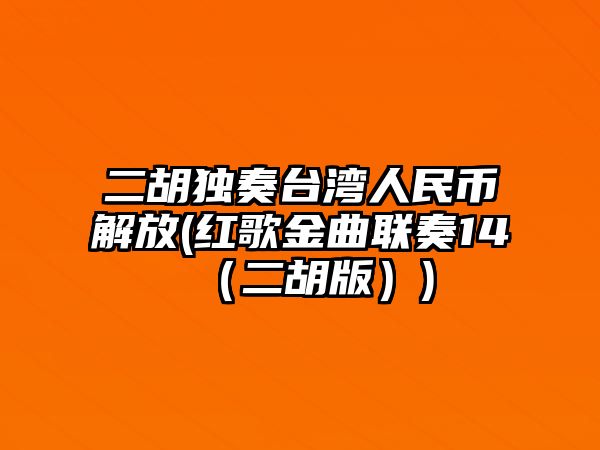二胡獨奏濟公小調(職業哭喪人:見過太多生離死別)

3月24日,山西平遙,職業哭喪人三平正跪在靈前哭唱,主家給的賞錢夾在孝帽里。

3月23日,山西文水縣,一個葬禮上,三平用下巴將一根大木棍頂在空中,木棍的頂端還頂著一輛自行車。

3月24日,山西平遙,一場葬禮正在舉行。

3月23日,山西文水縣,一個葬禮上,三平正表演吞氣球。
“媽媽啊,媽媽,今天你就要離開我們了……”
三平哭唱的聲音,如同暴風雨來臨前投下的悶雷,震得人心顫。
他上身披著白布,頭上系著白布,跪在了用PVC塑料材質搭成的靈堂前,鋪在院子里的氈布散落著稻草,空氣中彌漫著煙灰的味道。
三平翻著白眼,似乎因為太過悲傷而昏厥過去了,一只手也耷拉著。一旁的男子見狀,連忙伸出了手,掐住三平的人中。
“好!”圍觀的人群中有人鼓起了掌,手機咔嚓咔嚓拍照,人們笑著,在這場喪禮上看著三平的表演。這是當地一種流傳很久的風俗——哭喪,三平是被雇來的哭喪人。
“醒過來”的三平,繼續著悲慟的哭喊聲,而主家及其親戚朋友,則將“賞錢”,一張接一張地塞進三平頭上白色孝帽夾住,100元,300元,600元……三平頭上孝帽下的錢,最終定格在1000元。
“三平你剛才是真的哭暈過去了嗎?”
“不是,是演的,演悲傷過度暈過去了。”對于自己成功的表演,三平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半路出家的哭喪人
因為唱哭的本領得到了很多人認可,三平漸漸成了喜宴不歡迎的唱戲人。
今年57歲的三平,有著一米八的個頭,身體壯實,皮膚顏色是莊稼人常見的那種黝黑,鬢角微微發白,眼角的皺紋耷拉著,但是掩蓋不了他那雙大眼睛。整張臉上,最平淡無奇的,是他的那張嘴。薄嘴唇,上唇輕微上翹,干燥發白。就是這張嘴,說戲唱曲,用一段段哀嚎的哭聲送走陌生的亡人。
“我唱哭腔比較在行,所以大家都讓我唱。”隨著年歲的增長,三平也漸漸不再受喜宴的歡迎,也因為唱哭的本領得到了大家的認可,越來越多喪事的活兒找上門來。
三平哭喪,是半路出家。在此之前,他種過地,干過泥瓦匠,做過豆腐,也販賣過豬肉,農村里常見的幾種能養家糊口的營生,他幾乎都干過。2003年,國家開始嚴格管理生豬的屠宰,三平因為沒辦下來生豬屠宰證,只能放下了屠宰牲口的刀。
三平從小就愛好唱戲,扭秧歌。在不殺豬后,機緣巧合,有戲班子邀請他去唱幾句,那是他第一次走向舞臺。“當時我表演觀眾們挺喜歡的,我就想繼續表演。”三平后來就開始跟著戲班子一起表演,自學戲曲和雜技。
而最開始,他只是在戲班子里唱戲,唱著傳統的當地戲曲,表演雜技絕活逗人開心。戲班子在村頭表演,更多的時候,他們出現在結婚的喜宴,孩子的生日宴會,葬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第一次去哭靈,是被“主家”(指雇用戲班子的雇主)要求的,事情過去了十多年,三平已記不清當時的具體情況,但還是深刻記得自己當時的感受:“不情愿,覺得丟人”。
盡管不情愿,三平還是硬著頭皮走到了靈前,唱了一首《小寡婦上墳》。“我不能拒絕啊,因為我拒絕了整個戲班子都會難做啊。”在三平看來,去哭靈不是自己的本意,他是被架到了那個臺子上,由不得他。
“好像天生就適合干這行”
在農村戲班子,很多人都是吹拉彈唱樣樣都會,三平也是如此。
“咿咿呀呀……”
李東被電視里的聲響吵醒了,睜開雙眼,窗外還是一抹黑,但屋里的燈已經亮了,父親三平坐在床頭,眼睛直愣愣地盯著電視機,手握著筆在本子上抄寫著,嘴里念念有詞。
李東抬頭看了一眼墻上的掛鐘,凌晨五點,便翻了個身,模模糊糊又睡了過去。
從父親清晨日復一日的舉動和同學們的言語中,李東漸漸明白父親在戲班子的工作。那時他覺得父親的工作丟人,在學校里,時不時會有同學笑嘻嘻地走到他面前,“李東,我看到你父親昨天表演了,他在臺上牽著女人的手呢。”李東憋紅了臉。
他更害怕父親出現在學校,怕父親在教室門外用那一雙滴溜溜的大眼張望,加上面部表情夸張,總是能吸引同學們的目光,這些都困擾著當年才十來歲的他。
但正是這夸張的表情,浮夸的動作,讓三平在同行之間脫穎而出,幾乎每天,三平都能接到活。三平覺得,自己天生就適合干這行,他擁有生動的面部表情,響亮的歌喉。
三平所生活的山西,有著在喪事上面請樂隊戲班子吹拉彈唱送亡人的習俗,當地人認為這樣能讓亡人歡歡喜喜從陽間走向陰間。一般,按照當地話來說,一個戲班子,得包含著“敲打,哭的,唱的。”敲打指彈奏電子琴,打鼓,吹嗩吶等等各種樂器的人,唱的就是指唱戲,唱歌的,而哭的就是指像三平一樣的能夠在靈堂前哭喪的人。大多數時候,一個人總是能夠身兼多職,許多人都是吹拉彈唱樣樣都會。
三平也不例外,哭喪是后學的,最早的時候,三平唱戲,扮丑角,自己摸索著表演雜技。他的下巴和嘴唇的連接處,比面部其他地方的皮膚要暗沉,摸起來有粗糙的塑料感,那是經年累月頂凳子、自行車、木樁形成的繭。
“只有三平有這么多裝備”
三平的包包里,裝著表演要用的一干物什兒:口紅、牙膏、眉筆、乞丐服……
在戲班子里,除了吹拉彈唱,三平還有著自己的絕活兒。
他能用手掌拍碎一塊磚頭,不到1秒;他可以用下巴頂著重100斤的十個鐵凳子,堅持40秒;他也可以用下巴頂著自行車,堅持50秒;他還可以用鼻子把自行車輪胎吹起來,只用2分鐘……
除了嘴巴,三平的鼻子、眼睛、耳朵,都“會”抽煙,唱曲的過程中,三平會把煙點著,放在嘴里象征性抽幾口,用眼皮夾著,然后又把四五根煙同時塞到一個鼻孔中。十幾根煙一起點著后,三平將它們一起握著,將點著的香煙快速地往舌頭上摁幾下,就全熄滅了。
長長的氣球被慢慢塞進三平的嘴里,似乎直接進了肚子,圍觀的人們露出了驚恐的神色。有人跪在舞臺前,直直盯著三平的大嘴,想要知道氣球去哪里了,卻無法尋到破綻。
掀開三平的上衣,肚皮上一條10厘米,一條20厘米的疤痕顯現出來,那是用肚子吸附鐵碗掛重物留下的。眉梢,一小塊紅色的疤痕,來自表演雜技時不小心的走火。
在三平看來,他做的這些雜技表演,是藝術,應該受人尊敬,而他自己也表現出了對于這份藝術的尊重。
唱戲曲《勸吃煙》,表演一位教書先生,他提前會化妝。化妝的工具簡陋,一管牙膏,抹在鼻孔和眼角下,作為鼻涕和眼淚,來表現“日本鬼子來了后,教書先生吸鴉片上癮的精神萎靡。”煙盒里的錫紙被他別在帽子上,表演時拿出來,就成了吸食鴉片的工具。
身上穿的乞丐服是用破布一塊塊縫的;兩塊錢一支的口紅,三平買了兩個色號;一塊錢一支的眉筆,是他在平遙城里的商店買的。因為今年是豬年,三平還專門花了20多元,托人在網上買了一個豬八戒的面具。用雞毛扎成的濟公的扇子,用了十多年,濟公的帽子就用自行車車墊的布套子來充當,里面加固上鐵絲。
“在這個行當里,只有三平會有這么多的裝備。”同行這樣評價他。而三平也自豪于自己的表演,他覺得對自己有著“職業上的要求”。
不愿意主動去靈前“哭”
對于哭喪,三平一直沒有改變態度,只要主家不要求,他肯定不會主動去。
在同行之間,存在著鄙視鏈,哭喪處于鄙視鏈的最末端。雖然這是每個戲班子都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人們都瞧不上“去靈堂前哭。”
三平自己也瞧不上哭喪這活兒。“這丟人,是被人瞧不起的,主家不要求,我肯定不會主動去!”雖然已經干了十多年了,但是三平的態度還是沒有改變。
“三平叔去做這也能理解,他有兩個孩子。”和三平熟識的劉弘這樣評價他。劉弘是個90后,會各種樂器,還做著攬事的中間人,但他也不愿意去哭喪,“給多少錢都不去!”
28歲的董鵬卻和他們的觀念不同,只要給錢,哭不是事。董鵬和三平分別是兩個戲班子里“哭”的那個角色。
董鵬和三平在一場葬禮上“碰”上了。一般,主家有錢,兒女孝順,想要把葬禮的排場弄大一點,就會請多個戲班子在葬禮上表演。
“哇哇哇……”董鵬脫去了上衣,頂著一頭褐色大波浪假發,頭頂系上了一根白布條,直接跪在了事主的家門口,扯著嗓子嗷嗷哭了起來。他不唱曲,就是扯著嗓子干嚎,手里還端著一個鐵盤子,時不時往前伸一伸——要錢。
“讓他回去吧。”事主見狀連忙跑出來,對著他們戲班子里管事的人耳語。
一張一百元的鈔票被遞到了董鵬的手里,董鵬張著嘴愣了一下,便快步回到了屬于他們的戲班子搭成的舞臺上,又把嗩吶塞進了嘴里吹起來。
在另一個戲臺子和董鵬對吹的三平,看不上董鵬的這種行為。“這是下等的。”三平皺著眉頭,“他就是為了要錢呀。”
劉弘也瞧不起董鵬的行為,“他年紀輕輕的。”
類似這樣的話,也傳到過三平和家人的耳朵里。不過干了十多年的三平,已經不在意這樣的話,“大家是尊敬我的,我臺上唱戲,臺下做人,沒有人來質疑我的人品。”
今年28歲的董鵬沒有三平這么強的自尊。“我上去就是為了要錢啊。”董鵬笑了,他毫不避諱這一點,只要主家大方,上靈堂前哭一下,拿個千八百塊錢不是問題。父親去世后,董鵬看著父親舍不得花錢就這樣過完了一生,覺得人生也就是那么一回事,現在他該花錢花錢,只求過得開心。
而活了大半輩子,也算參透了生死的三平依舊節約,勤勞,就像每天按時外出覓食的鸕鶿,抓獲了魚兒,回到家中,再吐出來,哺育妻子和兒女。
供養兩個孩子長大,靠的都是三平送靈掙來的錢。雇主的賞煙,他從不抽。妻子會拿著這些幾十元的“好煙”去村頭的小賣部,換來些柴米油鹽。三平就花錢買兩塊錢一包的煙,在一天工作完后,看視頻的時候抽著解悶。
三平覺得自己不需要注重物質上的享受,他來這世上走一遭,要干的事情很明確:“人的使命就是贍養老人,養育兒女。”
見過了太多死亡
妻子兒女似乎都沒見過三平哭,即便他會在陌生人的葬禮上哭喪,也不會有眼淚。
三平是一個傳統的老父親,默默做事,不會用言語表達自己對于親人的情感。沒有對妻子說過我愛你,不會在兒女的生日說上一句生日快樂。
妻子和兒女幾乎都未曾見過他哭泣,雖然他會在陌生人的葬禮上哭喪。妻子唯一印象中有那么一次見到三平哭,是父親去世。
妻子聽到了三平的呼喊,跑進了東屋。
“你……快抱著他給他捋一捋。”三平站在床邊上,著急地對妻子說。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因為胃癌的折磨,父親已經不能進食了,妻子抱著干扁瘦弱的父親,手掌能清楚地摸到他后背凸起的肩胛骨。
突然父親張大了嘴,呼嚕一聲,就咽了氣。
妻子轉過身,看到了三平滿臉的淚水。
“你覺得死亡是什么?”
“就是沒了,這個人就消失了。”
“那你相信有來世嗎?”
“沒有,沒有來世沒有靈魂沒有陰間。”
從事哭喪,三平見過了太多的死亡。人們死亡的原因不盡相同,“燒死的,淹死的,上吊自殺的,被車撞死的,我都見了。”親屬們傷心的程度有著高低之分,葬禮的排場也因為家庭的經濟實力兒女們的孝順程度劃分出了不同的等級。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丁的突然離世,親屬們最難接受,遇見這樣的情況,三平也會傷心,“我可憐他還沒長大的娃娃。”
但大多數時候,三平并不會主動詢問死者去世的原因、年齡和家庭成員的情況。死者的生平在送靈人這里模糊,而葬禮的排場卻能真實地感知,許多時候,這關系到他們今天能夠拿到多少賞錢。
一位煤老板家花上千萬專門修通往山上墓地的路,賞錢兩三千地遞。而無兒無女的尸體被發現在其獨自居住的屋內,村委會的人把尸體放進最便宜的柳木棺材,推著推車埋到地里,沒有葬禮,也沒有碑文。
3月22日,三平又被邀請到一場葬禮表演。
一張一百元人民幣,被一只手高高舉過頭頂。拿著鈔票的男子大喊著“死者的朋友送上了100元。”隨即,這張紅色鈔票被塞到了麥克風的支架上。圍成一個圈的鼓、嗩吶、二胡、笙、鈸、電子琴演奏的節奏密集地撞擊著圍觀人群的心臟,樂手們的雙腳一上一下踩著拍子,鈸手的上身隨著鈸敲擊節奏左右擺動著。
地上的黃土揚起,風來了,吹翻了倚靠著麻繩排成兩列的花圈。跪在死者棺材一頭一尾本來沉默的兒女,開始大聲哭泣起來。
“唱首歌送我們的兄弟最后一程吧!”又是一張一百元被遞上。
三平拿起了話筒,站在樂手們中間,“呀呀呀呀呀,兄弟啊。”三平用哭腔嘶吼著,雙目緊閉,面部肌肉繃緊,褶皺從眼角一直蔓延到臉頰,手臂不時擦拭著眼睛。
“兄弟啊兄弟!”撲通一聲,三平跪向了靈堂的方向,右手直直地伸向了棺材的方向……
(文中劉弘,李東為化名)
A06-A07版采寫/新京報記者劉思潔
A06-A07版攝影/新京報記者尹亞飛
下一篇
二胡怎么能拉出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