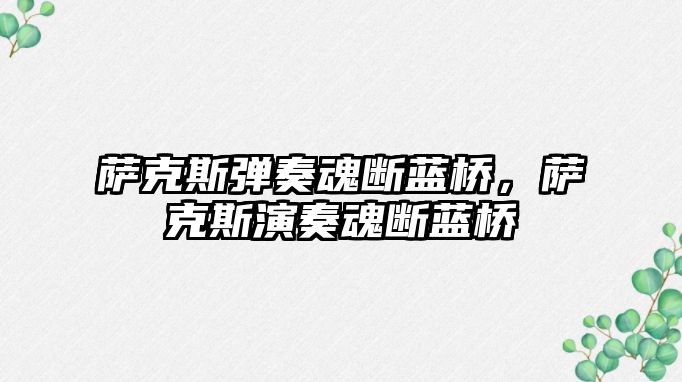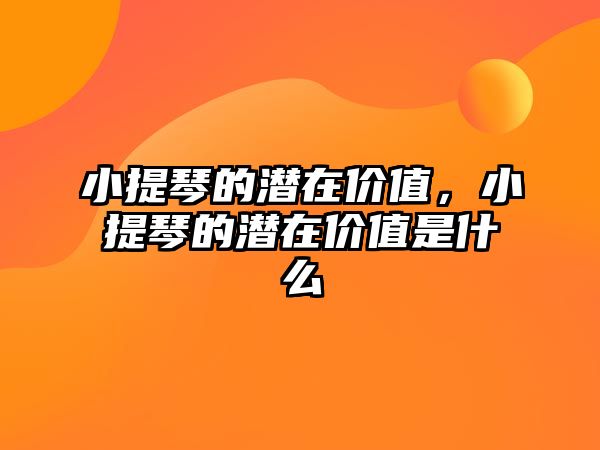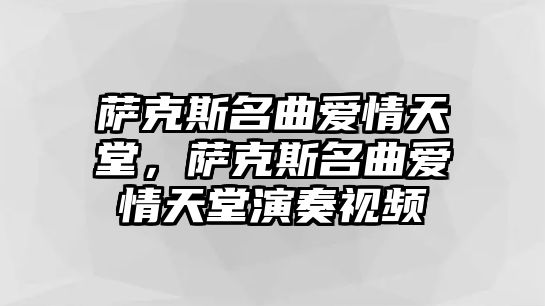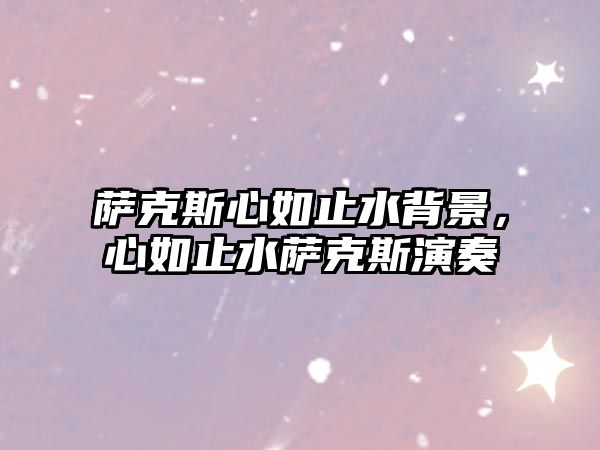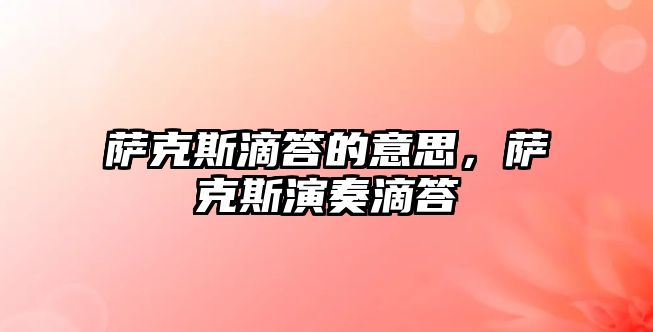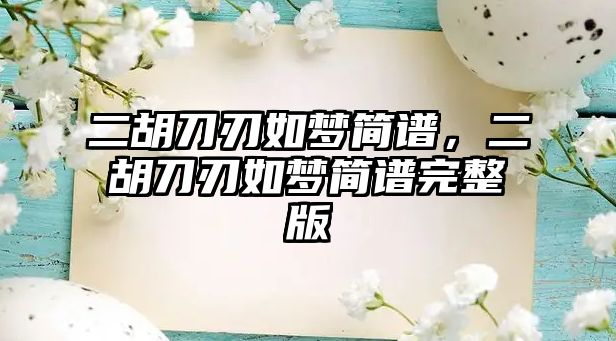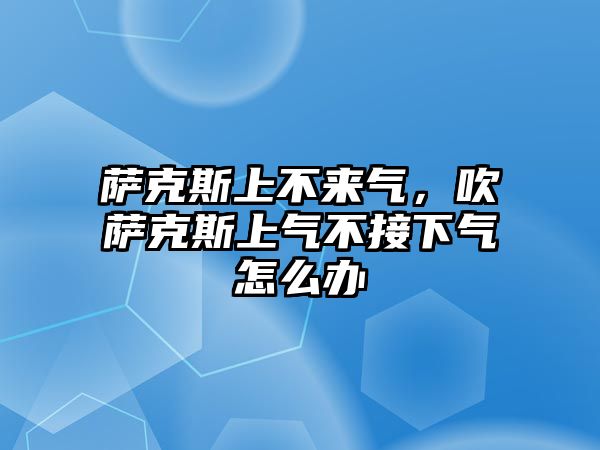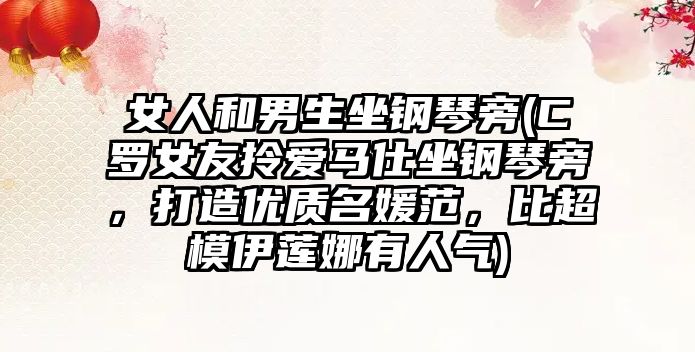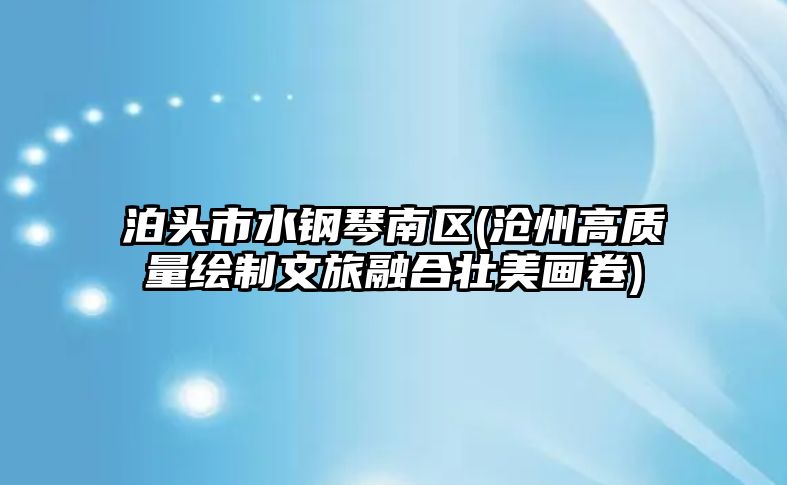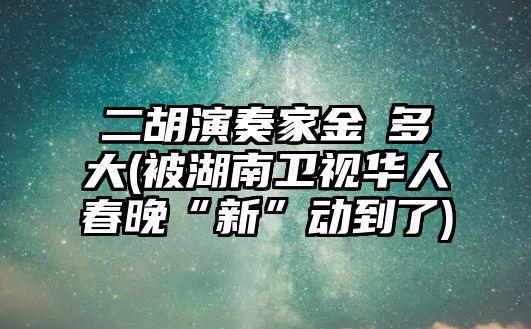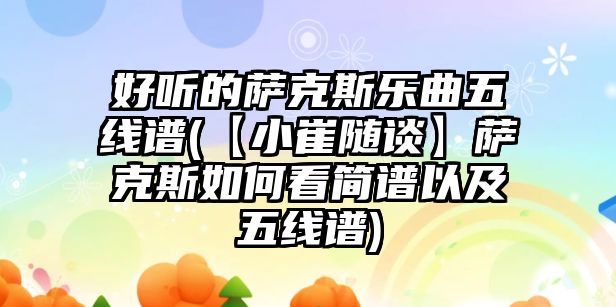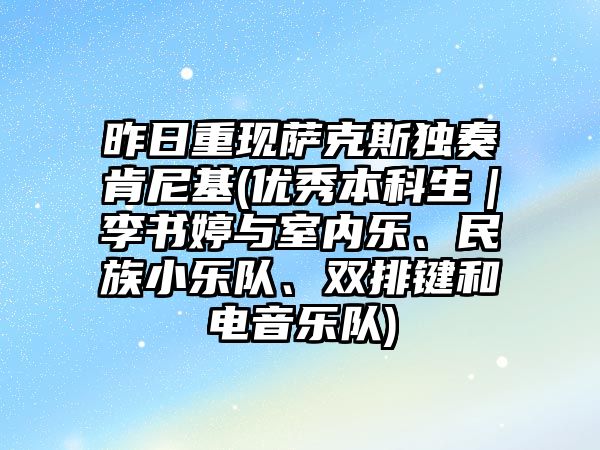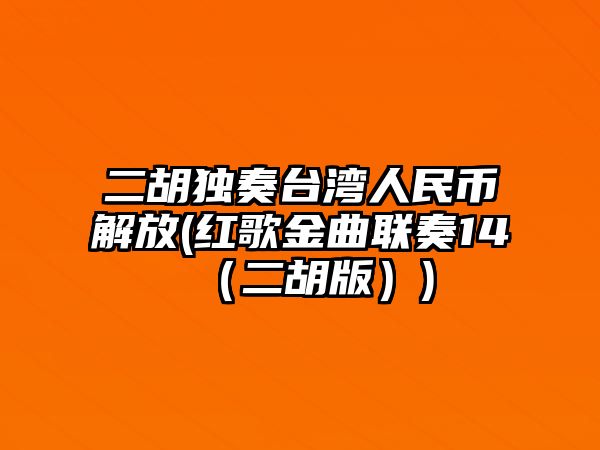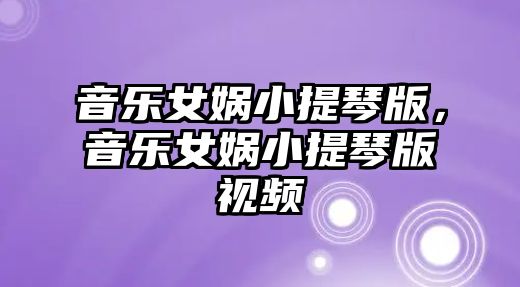小提琴G大調巴赫(小提琴家寧峰挑戰“巴赫無伴奏”,演出前我們和他聊了聊)

巴赫《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及組曲》素有“小提琴圣經”之稱,無論在哪個年代,都是全面考驗小提琴家演奏技巧和音樂素養的“試金石”,沒有十年八年的準備功夫,很難上得了臺。
10月10日晚在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小提琴家寧峰便將在一個晚上的時間里,挑戰巴赫小提琴音樂的巔峰之作。現場演奏加中場休息將近三個小時,無論對寧峰還是觀眾來說,都是馬拉松一般的挑戰。
雖然很早就在不同場合分別拉過這6首曲子,但直到前年,寧峰才開始以全套的形式挑戰巴赫無伴奏,在上海集中獻演更是第一次。
作為一位復調大師,巴赫的音樂始終是在多聲部中展開,也就是說這6首曲子的大多數樂章,同時有幾個聲部并存,需要演奏家同時清晰展現。比如《第二奏鳴曲》的第三樂章,完全就像兩位演奏家的二重奏,實際卻由一人奏出。
“小提琴獨奏作品極其少,大部分都有鋼琴或其他樂器在和聲上做補充,你拉巴赫無伴奏,首先要克服這一點,就像清唱一樣,但你又不能從頭到尾全是清唱,清蒸食物再好吃,大家吃多了也會膩。”
寧峰說,演奏巴赫無伴奏,演奏家要在非常局限的情況下展示小提琴最擅長的旋律,同時還要把伴奏的和聲做出來,這是很大的挑戰。另外,巴赫的音樂里有很多宗教成分,都是寫給上帝的,沒什么七情六欲,演奏家在克服技術問題后,音樂上還要表達出崇高的、神圣的境界,這也是難點所在。
對寧峰來說,演奏巴赫無伴奏,腦力上的挑戰比體力上的挑戰大得多,因為必須全程高度集中、高速運轉,演完之后,他不會馬上感覺累,反而很興奮,往往要到第二天,才會真正有疲倦的感覺。
一位樂迷說,這樣一套曲目必須交給一位真正擔當得起的演奏者,否則,還是不聽這樣挑戰極限的全集為好,而寧峰的巴赫無伴奏,讓他產生了不容錯過的想法。究其原因,“無非是我感到他是當代極少數能夠擔當——在一個高水平上勝任——這套曲目的小提琴家。”

寧峰
學生要學會“舉一反三”
演奏家之外,寧峰還有一個身份是老師。2011年前后,常居德國的他開始在柏林音樂學院教授小提琴,教學與演出兩不誤。
也因此在上海演出的前一天,主辦方特別安排了一堂大師課,讓琴童與寧峰面對面交流。5組學生依次上臺,有小提琴獨奏,也有室內樂組合。針對不同學生的不同問題,寧峰深入淺出,總能給出在場所有人都能聽得懂的建議。
現場,一位學生拉了一段維爾瓦第《四季》第三樂章“夏”,其中一些樂句讓人聯想到夏日里的暴風雨。寧峰問他,形容暴風雨的詞匯有哪些?學生想了想,答“傾盆而下”,“暴風雨的速度又是什么樣的?非常快,所以樂譜里標注了‘急板’。將來對曲子更熟悉了,你的速度可以更快一些,你現在不像暴風雨,只是普通的大雨,還沒有風。”
還有三位學生分列鋼琴、小提琴、大提琴,合奏了一曲德彪西《G大調三重奏》。寧峰先是向他們普及了德彪西不同時期的作曲風格,以及什么是法國印象派,隨后話鋒一轉,講到了室內樂的合作問題。
“室內樂最主要的一點,你多數時候都是在襯托別人,不是主角,你要有自知之明。另外,你不光要搞清楚自己在演奏什么,還要搞清楚別人在演奏什么,要隨時觀察,隨時預判合作者的變化,根據他們的變化做出調整,所謂‘一心二用’。”但是,輪到自己唱主角、自己是絕對中心的時候,“你是紅花,別人是綠葉,就像‘聚光燈’打在身上,你可以有更多的表現。”
當上海音樂學院一位本科三年級學生演奏了門德爾松《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后,寧峰的要求顯然更高也更細了。
“他們還在業余學習階段,你是本科學生,要求要更高。就像切土豆絲,自己家里炒,粗一點細一點無所謂,味道差別好像也不是特別大,但在飯店里,專業廚師燒給客人吃,就要色香味俱全,每根土豆絲的粗細要有大致的規范。”
談到這里,寧峰又重申起小提琴里百年不變的音準問題,不管是誰拉,什么時候拉,這個問題都會相伴終身,永遠沒辦法解決,“音準就像圓周率,大家一般都記3.14,其實還可以往下數3.1415926,無限循環,音準沒辦法做到100%精確,但演奏者還是要盡可能去接近。”
另外,舞臺表演一般不會借助麥克風,為了讓觀眾清楚地感受到表演者的意圖,各方面都必須更夸張,“就像主持人化妝,你會覺得粉很厚,看著像假人,但燈光打上去剛剛好,在舞臺上正合適。同樣,在演奏的時候,你在音樂上的強弱對比、情緒變化,也需要多好幾個檔次,要更明顯。”
在德國,寧峰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都是一對一上課,如今正在帶的兩位學生,一位來自中國臺灣一位來自中國香港。
被問及什么樣的好苗子會讓他眼前一亮,寧峰坦言,一個學生一開始讓人眼前一亮,不見得會一直亮下去,反之亦然。
在他看來,學音樂的才能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對音樂和樂器的敏感、直覺,那種與生俱來的親近,這是天賦;一方面是后天的努力和學習,有些人可能對音樂和樂器有天生的直覺,但并不一定擅長學習。
在國外,學小提琴的人從本科、研究生念到演奏家文憑,一共8年16個學期,要想學完所有小提琴作品是不可能的,所以寧峰始終認為,學生最重要的是學會“舉一反三”,將來才有自我教育的能力,但教學這么多年他發現,有些學生雖然很有天賦,但事事需要老師提醒,不會通過老師以往的講解,自主分析、自主解決新作品里遇到的問題,這都會制約他將來的發展。
怎么才能當一個好老師呢?
寧峰形容,音樂是一種“感受”的教學,哪怕是語言學家,也很難去客觀地、貼切地形容這種感受,老師首先要把這種感受教給學生。
“比如弦樂里華麗的、明亮的、溫暖的音色,老師要先把這種音色拉出來,再讓學生通過自己的雙手去模仿,然后再從作曲家當時的創作環境、創作背景等開講,告訴他們這里為什么需要華麗的、明亮的、溫暖的音色,為什么需要悲傷的、歇斯底里的情緒,從理論上去支持我們的表達。”

不鼓勵為了得獎而比賽
在成為職業演奏家之前,寧峰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建院兩百年來第一位滿分成績畢業的學生(2003年),以及第51屆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比賽冠軍得主(2006年)。
1999年到2006年,寧峰以每年一到兩個比賽的頻率,以一個小提琴學生的身份頻頻亮相國際賽場,帕格尼尼金獎最終為他的參賽之旅畫上一個圓滿句號。
回憶起當時頻繁參賽的原因,寧峰向澎湃新聞記者回憶,最實際的原因是經濟問題。
1998年,寧峰以全額獎學金的身份入讀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然而獎金只解決了學費,衣食住行都要靠自己解決。
“家里為我去倫敦上學竭盡了全力,倫敦現在的物價對我們來說都很貴,二十多年前就更可怕了。我在倫敦租一個小房間,每個月至少3000塊人民幣,相當于一個成年人一份相當不錯工作的一個月工資。比賽得了獎就有獎金,我需要靠獎金幫自己生存下來。”
另一個原因在于,完成學校布置的學業任務,對寧峰來說太容易了,他需要通過比賽來給自己加壓,增加挑戰,畢竟,比賽的曲目量比學校里的曲目量大多了。
在他看來,學音樂的人一生會面臨三個舞臺:考試、比賽、音樂會。
“音樂會相對來說最容易,觀眾花錢花時間來聽音樂會,是來享受而不是受罪的,大家出發點是樂觀的,無形中會影響舞臺的氣場;考試呢,下面坐的是老師,老師找你的不足,目的是為了幫助你日后進步;比賽呢,下面坐的是評委,他們的工作就是你不夠好就扣分,來比賽的人都是你這個年齡段里最拔尖的,大家是競爭關系,所以壓力最大,經歷過那么強的壓力,你將來再面對別的舞臺會駕輕就熟很多。”
2020年8月,受上海艾薩克·斯特恩國際小提琴比賽邀請,寧峰也要坐鎮評委席,位列13位評委之一。
他個人非常鼓勵年輕人參賽,但前提是,年輕人要想清楚,比賽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為了得獎,并不提倡。
“體育比賽有明確的輸和贏,評判有明確的標準,但藝術類的比賽沒有標準,一首作品我這樣演奏,不代表別人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演奏。兩個選手比賽,其中一個用更符合我的審美觀念的方法演奏,我很自然會給他更高的分數,但并不能說明另一個選手差,只是我在評委席上必須要做一個選擇。所以比賽如果是為了得獎,我不贊同,如果是為了鍛煉自己、提高自己,我絕對支持。”
寧峰笑說,參加過那么比賽,他的簡歷里寫出來的,肯定是最光彩的,但一個人不可能只有光彩的經歷,讓他感悟更多、感觸更深的,往往是那些不那么成功的經歷。
“人這一輩子不可能永遠成功,面對更多的是失敗的經歷,你怎么去面對這種挫折感,不把這種挫折感變成悲觀的情緒,而是變成動力,能夠做到這一點已經是很大的成功了。”
這種良好的心態,來自父母對他的積極影響。寧峰的學琴之路并不是他主動選擇,而是父親要求的,父親希望他將來能有一個愛好,不要求學好,但至少不能學壞,也從未表露過希望他得獎的愿望,所以他從小就沒有這樣的壓力——如果成績不好會對不起家長、對不起老師,他后來對自己的要求,也不是比賽必須得獎、考試必須第一名,只要努力過了,不管什么結果,都不會后悔。
2006年,寧峰拿到了人生中份量最重的帕格尼尼金獎,“那時候我已經25歲了,已經算是‘高齡’了,我的同齡人十幾歲就開始得獎了,含金量也很高。在我這一批中國小提琴家里,我在比賽里出成績絕對是最晚的一個,但我知道,只要我努力做了,沒有遺憾,就OK了。如果不能成功,我肯定還有別的路可以走。”
在德國教書的同時,寧峰如今一年演出80-90場,40%在歐洲,30%在中國,余下30%在北美、東亞等地方。
在不少樂迷眼里,寧峰是一位當代技巧名家。翻看他的錄音曲目就能知道,他對真正蘊含“超絕技巧”的小提琴音樂的熱衷,當代少有人能比。而他那出眾的發音與運弓技巧,最終成就了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吸引無數人為之折腰。
寧峰對澎湃新聞記者強調,演奏家要在舞臺上生存下來,技術過硬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則就不要吃這碗飯,保持好技術狀態,是他平時必須做的功課,“做完功課后,如何用這么多年積累下來的技術能力去把音樂表達出來,是我接下來的目標和要求,不管20歲、30歲還是40歲,都不會變。技術永遠是為音樂服務的,只有在技術上做到極其的精確,才能在藝術上獲得最自由的發揮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