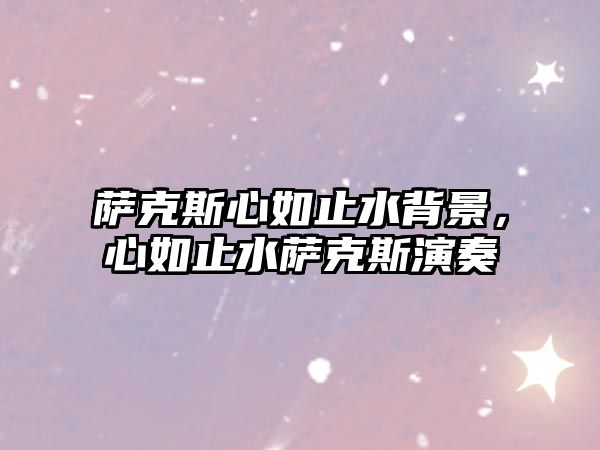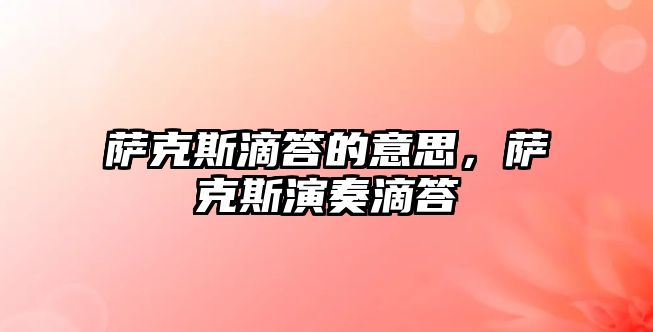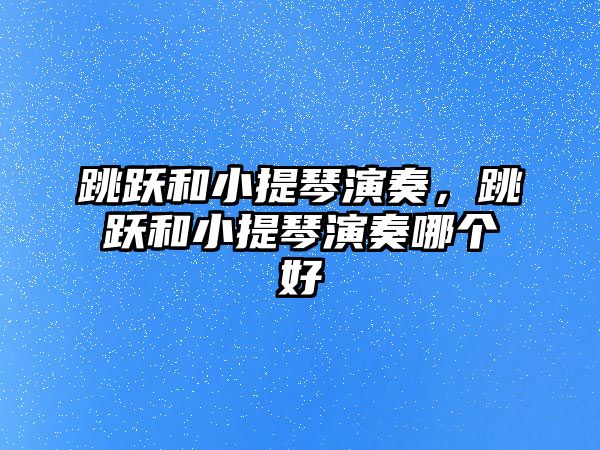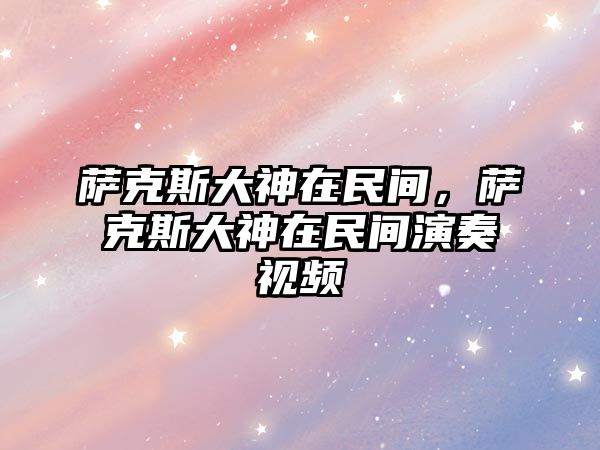小提琴中國專訪(專訪小提琴家寧峰:把紙上的音符在手中變活)
近日,在上海交響樂團2020-2021音樂季開幕音樂會上,知名小提琴家寧峰與指揮家余隆執棒的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繹了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緊接著,他又與鋼琴家黃秋寧合作了全套的貝多芬鋼琴與小提琴奏鳴曲。
常年活躍于國際舞臺的寧峰,對音樂始終懷著一種謙遜與敬畏。在與記者的對話中,他袒露了自己打動觀眾的“秘訣”。
人物
寧峰說,自己是一個特別普通的人。出生于成都的他,父母都沒有學過古典音樂,讓他學小提琴,只是為了陶冶情操。
學琴之初,寧峰因左手小指太短,先天條件不好,吃過不少“閉門羹”。“我從小到大都是在挫折中長大的,我感恩那些失敗的經歷。”
18歲時,寧峰考入四川音樂學院,并在此后赴柏林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和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深造。在畢業獨奏音樂會上,他拿到了滿分,成為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近兩百年歷史上第一位在畢業音樂會上拿到滿分的學生。
2006年,25歲的寧峰參加國際小提琴領域的最高賽事———第51屆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比賽,并摘得桂冠,他因此獲準演奏帕格尼尼生前演奏過的瓜內里名琴。
從此,寧峰躋身國際一流小提琴演奏家之列。他的演奏以絲綢般的質感、飽滿的抒情性、高超的演奏技巧和強大的感染力著稱,在國際樂壇受到認可。
如今,寧峰在他的母校柏林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任教。雖然長居德國,但他依然是中國國籍。他說,能在2020這個特殊的年份回到祖國,成為上海交響樂團新音樂季的駐團藝術家,對他來說是永生難忘的經歷。

做作曲家與聽眾的仆人
上觀新聞:您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說,這次與上海交響樂團排練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時,聽著樂隊在身后演奏,覺得自己“雞皮疙瘩掉了一地”。為何會有這種感覺?
寧峰:當音樂打動人心靈的時候,人一般會有兩種反應,一是流淚,另一種就是起雞皮疙瘩。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太偉大了,再加上余隆總監排得非常細致,上海交響樂團的演繹很認真。當音樂發展到高潮的時候,我真的是心潮澎湃。
上觀新聞:這種感覺是可遇不可求的。
寧峰:有時候我在臺下聽音樂時也會有這種起雞皮疙瘩的感覺,但作為演奏者參與音樂創作的時候,我會要求自己盡量冷靜。因為我需要在思想上高度集中,控制好手中的樂器。如果完全被音樂打動,就容易走神,可能會在技術上出現失誤,作為現場演奏來講,這是要盡量避免的。但是這次排練包括正式演出時我是真的被音樂打動,被上交音樂家們的狀態打動,同時也激發了我想要更好地表達音樂的欲望。
其實,我跟余隆總監還有上海交響樂團曾經合作過很多次,但這次是作為駐團藝術家來演奏,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大的激勵。
上觀新聞:為何會選擇《我和你》作為這次上交新音樂季開幕音樂會的返場曲目?
寧峰:今年3月,我跟余隆總監討論返場曲目的時候,就在想能不能演奏一部作品,用非常溫柔的方式來團結大家、鼓舞大家。《我和你》是陳其鋼老師為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創作的主題歌。那一年,我們也經歷了一些災難,但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和你,心連心,永遠一家人。”我們希望能夠用音樂讓大家一起努力,克服種種困難,向往美好的明天。
上觀新聞:不同的演奏家在舞臺上會營造出不同的氛圍。繼開幕音樂會后,您還演繹了貝多芬的鋼琴與小提琴奏鳴曲全集,這對您和觀眾來說都是一種挑戰。您希望自己的音樂會給觀眾帶來怎樣的氛圍或者感受?
寧峰:10首貝多芬的鋼琴與小提琴奏鳴曲我們是分三場音樂會來完成的,對觀眾來說,就像是閱讀一部名人自傳一樣。我希望通過自己以及我的鋼琴合作者———鋼琴家黃秋寧老師,在作曲家與觀眾之間搭起一座橋梁,讓大家能夠感受到音樂的偉大。
我對自己有一個定位,就是做音樂的仆人。這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我是作曲家的仆人,我需要通過學習作曲家的語言以及譜面上所有的標注,去體會、理解作曲家想要表達的意圖。另一方面,我是觀眾的仆人,我要把作曲家寫在紙上的音符,通過我的雙手變活。

寧峰與黃秋寧合作貝多芬鋼琴與小提琴奏鳴曲全集
他用最簡單的音符,創造偉大的旋律
上觀新聞:今年是貝多芬250周年誕辰,您心目中的貝多芬是怎樣的,他的作品為何到現在依然能夠打動人心?
寧峰:貝多芬用最簡單的語言創造出了最偉大的音樂。比如《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的“歡樂頌”,主旋律其實總共就5個音,但這簡簡單單的5個音創造出了最貼近人類心靈、最博愛的旋律。拿他的小提琴協奏曲來講,旋律的動機就是4個四分音符,簡單到不能再簡單了,但他就以這4個四分音符為基礎,勾畫出了一幅偉岸的圖景。
如果用建筑來打比方,那巴赫的音樂就像莊嚴的教堂,而貝多芬的音樂則如同偉岸的大廈。
上觀新聞:音樂是作曲家與演奏者內心的寫照。演奏家的內心對待音樂是功利浮躁還是平和謙遜,都會體現在音樂中。您的演奏中始終透著一種真誠與謙遜,您是如何保持這種狀態的?
寧峰:音樂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愛好。我一直對音樂保持著一種非常敬畏的心態,我覺得一個人無論從事什么行業,對工作的尊重或者說敬畏是必須的。
音樂是一門藝術,但對藝術的追求就像圓周率一樣,可以無限地精確下去。我們沒有辦法做到終極的完美,但需要不斷向完美的方向去努力。我想,保持這樣的追求與心境,會讓我演奏出來的音樂更純粹。
上觀新聞:小提琴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純美的樂器。
寧峰:是的,每一件樂器都有自己的特點,如果說大提琴的聲音帶有些憂郁的美,那小提琴就有一種非常純凈的美,而且它的歌唱性特別強。我認為,把這種純凈的美表達出來是最首要的。
當然,演奏是為了樂曲而服務的,作曲家希望表達出什么樣的聲音效果,我們就需要去尋找、實現那樣的聲音。當有些作品需要表達悲憤的時候,也要盡力去表現。

保持興趣比考級更重要
上觀新聞:您近年來在德國任教,作為老師,您覺得國外的音樂教育與我國主要有哪些差異?
寧峰:西洋音樂對于我們來說是一種外來文化,古典音樂與普通人的距離比較遠。但在西方國家,交響樂是他們自己的文化,在兩三百年前,古典音樂就是當時的流行音樂,所以相對來說,在國外學習樂器并不是一件特別高大上的事,學習的環境比較自然,學生的壓力也不會很大。
不過,壓力是一把雙刃劍。壓力太小,有些孩子就不會認真地學習;當壓力過大,尤其當孩子一心為了比賽或考級而學樂器時,心態就會變得比較功利。
在德國,學琴的孩子也會參加一些比賽,但大多數家長和孩子都沒有把這當成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主要還是為了玩而學習,他們對音樂一直保持著濃郁的興趣。中國孩子們往往練琴很刻苦,基礎也打得比較牢,但孩子容易失去對音樂的興趣,并不覺得演奏音樂是一種享受。所以,要掌握好一個度,既要認真練琴,但也不要把比賽或者考級作為學習音樂的主要目的。
上觀新聞:您在疫情期間錄制了維瓦爾第的《四季》,一人分飾16名演奏員,而且每個角色的形象都有所不同。這段視頻讓很多觀眾看到了一位幽默的提琴家,也讓人覺得音樂是一件挺有趣的事。能否談談您當時錄這段視頻的初衷?
寧峰:我認為音樂本質上是為了給聽眾帶來歡樂與享受的,這點跟電影或小說類似,當然有些非常深刻的音樂與電影除了娛樂大眾以外,還能給大家帶來一些感悟。
我從小到大主攻的是小提琴,但也陸續接觸了一些其他樂器,所以就想到把各種弦樂器湊在一起,錄制這樣一段有趣的視頻,在疫情期間給聽眾帶來一絲歡樂。
欄目主編:龔丹韻文字編輯:陳俊珺題圖來源:上海交響樂團
來源:作者:陳俊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