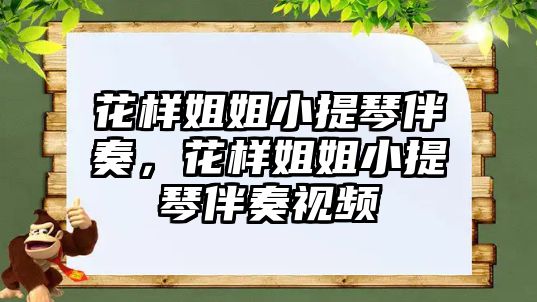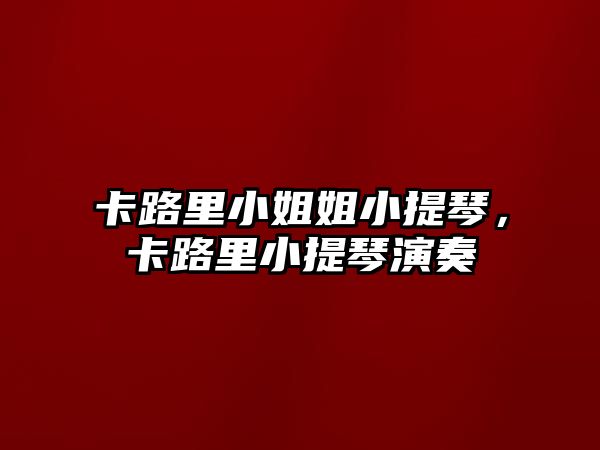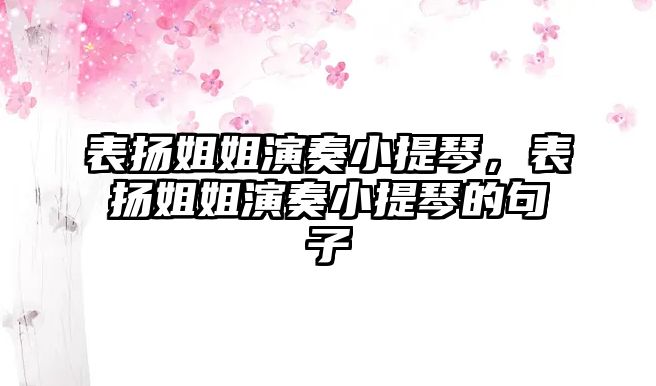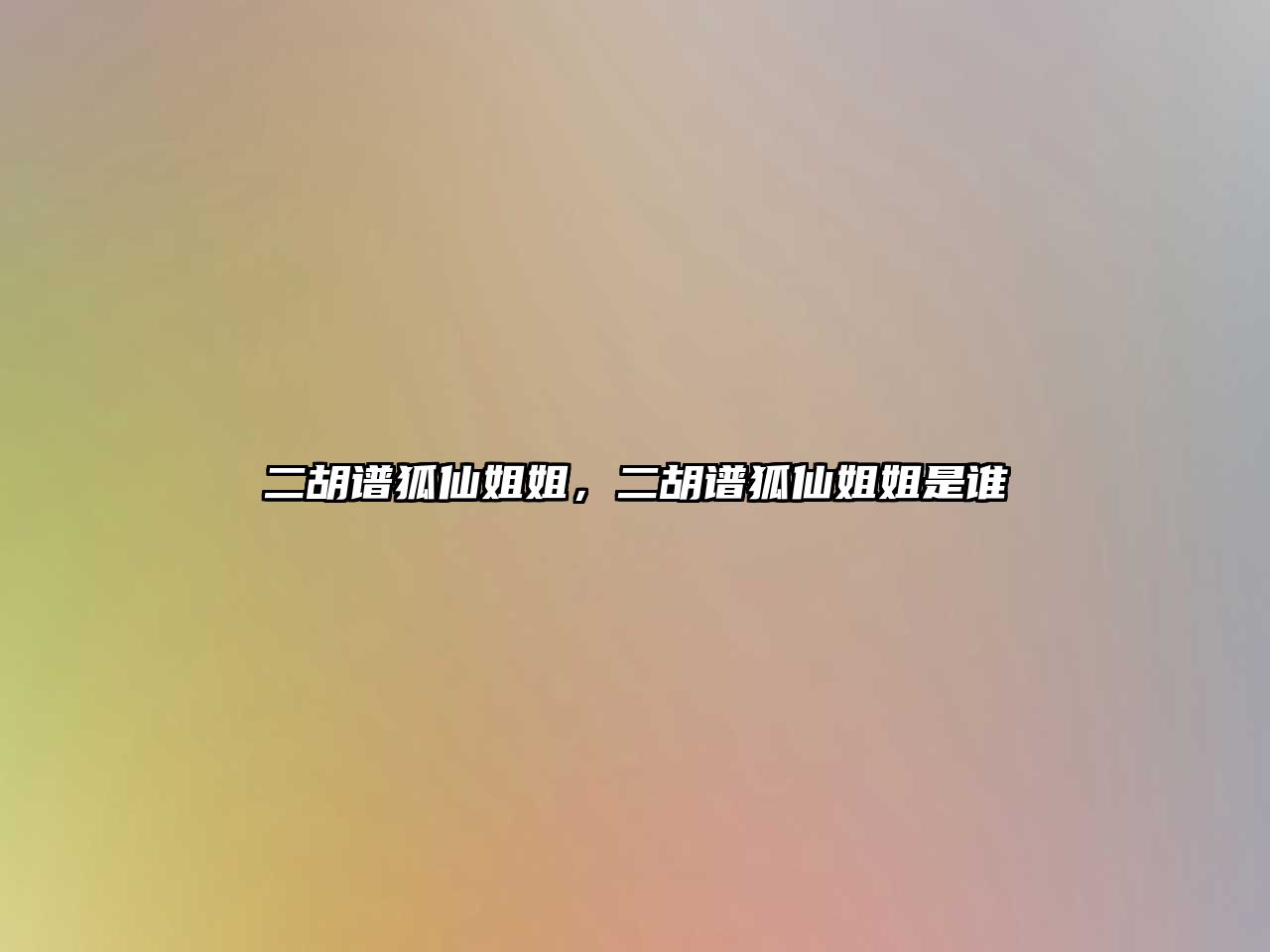舊夢薩克斯下載(盛夏的告別|順昌路上的薩克斯聲)
澎湃新聞記者李菁
視頻加載中...
【編者按】
聚散離合終有時。
2022年盛夏,上海成片二級舊里以下房屋改造收官,越來越多藏在市井煙火中的古老街區,與世人暫時道別。
順昌路、永年路、夢花街……它們從舊時光走來,承載鄉愁與遙遠的記憶;它們也在不斷追趕時代腳步,以改造提升實現城市更新。
風華不再,舊夢重拾。即日起,澎湃新聞推出“盛夏的告別”系列,記錄老街坊、小弄堂和沿街商鋪搬遷前最后的夏天。
老城廂或以新面貌歸來,煙火人家將各奔東西。有限的相聚時光,賦予離別應有的儀式。

江西飯店二樓,便是王禮珊的家。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李菁攝
走在順昌路上,常常可以聽見悠揚的薩克斯聲。
循聲而去,穿過網紅“蒼蠅館子”——江西飯店店面與后廚的間隙,走上狹窄的臺階,便來到了聲音的主人家。
聲音的主人叫王禮珊,今年68歲,她也是江西飯店的房東。上個世紀,王禮珊的祖父母從湖北來滬后扎下根來,生兒育女。自那時起,一家人就住在順昌路的這棟樓里。

王禮珊在家中吹薩克斯。
“走不出去”的姐妹
早年,祖父母在一樓開著百貨商店,王禮珊記事以后,百貨商店因為公私合營而關張,一樓的房間轉而用于居住。
王禮珊的父親是中學語文教師,母親在企業工作,倆人養育了六個孩子。王禮珊排老五,她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一個弟弟。小時候,一大家人住著兩層樓和亭子間,“那時候算擁擠的”。
后來,哥哥們搬出去租房子住,弟弟也去了南京發展。父母先是搬去哥哥在閔行買的房子,老房只剩下王禮珊和姐姐;再后來,哥哥賣掉閔行的房子,置換成了兒子的婚房,王禮珊的父母又搬回老房,直至去世。

在家中窗戶旁,可以看見順昌路的街景。
老房經歷了近百年的人事變遷,然而,王禮珊和姐姐卻“走不出去”。
姐姐比王禮珊大十歲,在三歲時,因發高燒服用過量藥物,大腦永久性損傷,變成殘疾,終生只能依靠別人照顧。
早些年,王禮珊和父母一起搭手照顧姐姐,父母年紀大了以后,照顧姐姐的擔子就落到了王禮珊一個人肩上。
“姐姐穿衣服不知道正的反的,洗澡也不會的,然后她現在牙齒一點也沒有了,她也不能裝,因為裝牙齒需要配合,哪里痛她也不會講。”王禮珊說。
平日里,姐姐需要專人細致的照料。“(姐姐)不像我們懂得哪里不舒服,她講不來的,要我們觀察到她有點不舒服了,再去看病。”王禮珊告訴記者,“基本上我照顧姐姐就不能出門,幾十年到現在,養成了習慣,出門反而感覺好像有負擔一樣。”
14年的租客
為了維持生活、照顧姐姐,一樓的門面房被租了出去。江西飯店是最久的租客,從2008年在樓下營業至今。租金不算多,每年稍微加一點,但是是家庭重要收入之一,也彌補了姐姐就醫和日常的花銷。
飯店開在樓下,還有一個好處是“不用開火了”。
“我們都是像自己人一樣的,我們不燒就從樓下盛一點來吃。”王禮珊說,“我們跟他們口味差不多。他們是吃辣的,我們湖北人也吃辣的。”

王禮珊父母年輕時和王禮珊哥哥、姐姐的照片。
王禮珊年輕時在閔行區的一家發電廠工作,因為是特種行業,45歲便提前退休了。如今獨身的她也曾有過一段婚姻,當時還在閔行安了家。但是,因需要回順昌路照顧姐姐,她與丈夫長期分居,最終分手。那時,他們的兒子十來歲。
之后,王禮珊也沒想過再找個伴兒。“習慣了,因為我也是每天忙忙碌碌,不是很寂寞的,要照顧我姐姐咯,還燒燒(飯)咯,吹吹薩克斯咯,好像生活過得還蠻快的。我們樓下開飯店蠻熱鬧的,如果搬了新房子可能就不一樣了,肯定要寂寞了。”
順昌路上的熱鬧讓她覺得,就算一個人也不感覺很冷清。
對于自己因照顧姐姐而被支配了的生活,王禮珊早已淡然處之。開始時,她也曾覺得,照顧姐姐這件事,“好像把我的生活打亂了”。而后來,她慢慢接受了這件事,“走到軌道里面就習慣了”,雖然“開心是談不上開心”,但至少每天的心境都很平和。
煙火氣中的日常生活
王禮珊的房間不過十平方米左右,干凈而整齊、沒有多余的雜物。墻壁上掛著一張書法作品、父母年輕時與哥哥及尚在襁褓中的姐姐的一張老照片貼在其中;父母金婚時的紀念照也掛在一旁。

王禮珊父母金婚紀念照。
如今,王禮珊的兒子38歲,兒子兒媳都是醫生,安家在徐匯,有兩個女兒。今年上半年上海疫情洶涌時,順昌路算是重災區,那時王禮珊和姐姐正巧住在兒子家中,平穩地度過了兩個月的封閉期。
“我覺得我其實比較喜歡老房子。”王禮珊坦言,順昌路的煙火氣,并不會讓她覺得吵鬧。

王禮珊在家中。
平日里,樓下的江西飯店幾乎24小時忙不停歇,“因為他們做夜宵,早晨還要進菜理菜,房間也要打掃衛生,這樣是不停的。”
“我就喜歡他們做生意。如果一到春節哦,他們回家了,我就有一種負擔了。上面下面都關掉,就感覺有點害怕了。”說到這里,她呵呵地笑,“就這種想法,最好他們不要回家了。”
此外,鄰里關系也讓王禮珊感到安心。“我們(鄰居)都蠻好的,在這里有感情的,幾十年下來了,基本上平時我門開了就下去了,不會考慮到有生人來拿東西。”在順昌路,王禮珊幾乎過著“夜不閉戶”般的生活。
隨著上海市最后一個成片舊改項目——建國東路68街坊及67街坊東塊的正式生效,順昌路上的住戶和店鋪已在陸續搬離中,王禮珊也不例外。
澎湃新聞記者探訪當日,王禮珊正和朋友一起打包家中物品,因為近日前來拜訪的人很多、搬家也雜亂,便帶姐姐去了哥哥家中暫住。

王禮珊與朋友在打包家中物品。
王禮珊有些擔心搬家后的生活,街坊鄰居不再熟識,家門口不再升騰著熱鬧的煙火氣,家庭收入也少了飯店房租這一重要來源。
另一方面,她也有了初步的安排。準備先帶姐姐去兒子家住下,等到征收款到位之后,在兒子家附近買一個小房子,方便互相照應。
花甲之年,自學薩克斯
2016年,母親去世后,之前從未接觸過樂器的王禮珊開始學習吹薩克斯,唯一的學習渠道是在手機上看視頻。六年多過去了,如今不少曲子她都能信手拈來。順昌路上人來人往,總有行人被這優美的旋律所吸引。王禮珊卻坦言,自己沒有音樂基礎,之前沒有接觸過樂器,年輕時唱歌都常不在調上。
她托朋友買了三把薩克斯——高音薩克斯、中音薩克斯、低音薩克斯。
照顧姐姐之余,閑來無事時,她便吹上一曲。《送別》《梁祝》等都是她所喜歡的樂曲。“喜歡吹比較有感情的旋律,帶一點傷感的,輕快的聲音吹得少。”
為什么會選擇薩克斯而不是其他的樂器呢?“感覺好像現在年紀大的都在學薩克斯什么的,我也就學了,薩克斯公園里都在吹。”她說。
但王禮珊卻從沒在公園里吹過薩克斯。她總是站在十平米的房間里,將薩克斯掛在胸前,把U盤插進音響,打開配樂,面朝窗戶吹起悠揚的曲調,給業已飽和的順昌路增添進一抹淡淡的哀愁。
責任編輯:高文圖片編輯:蔣立冬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