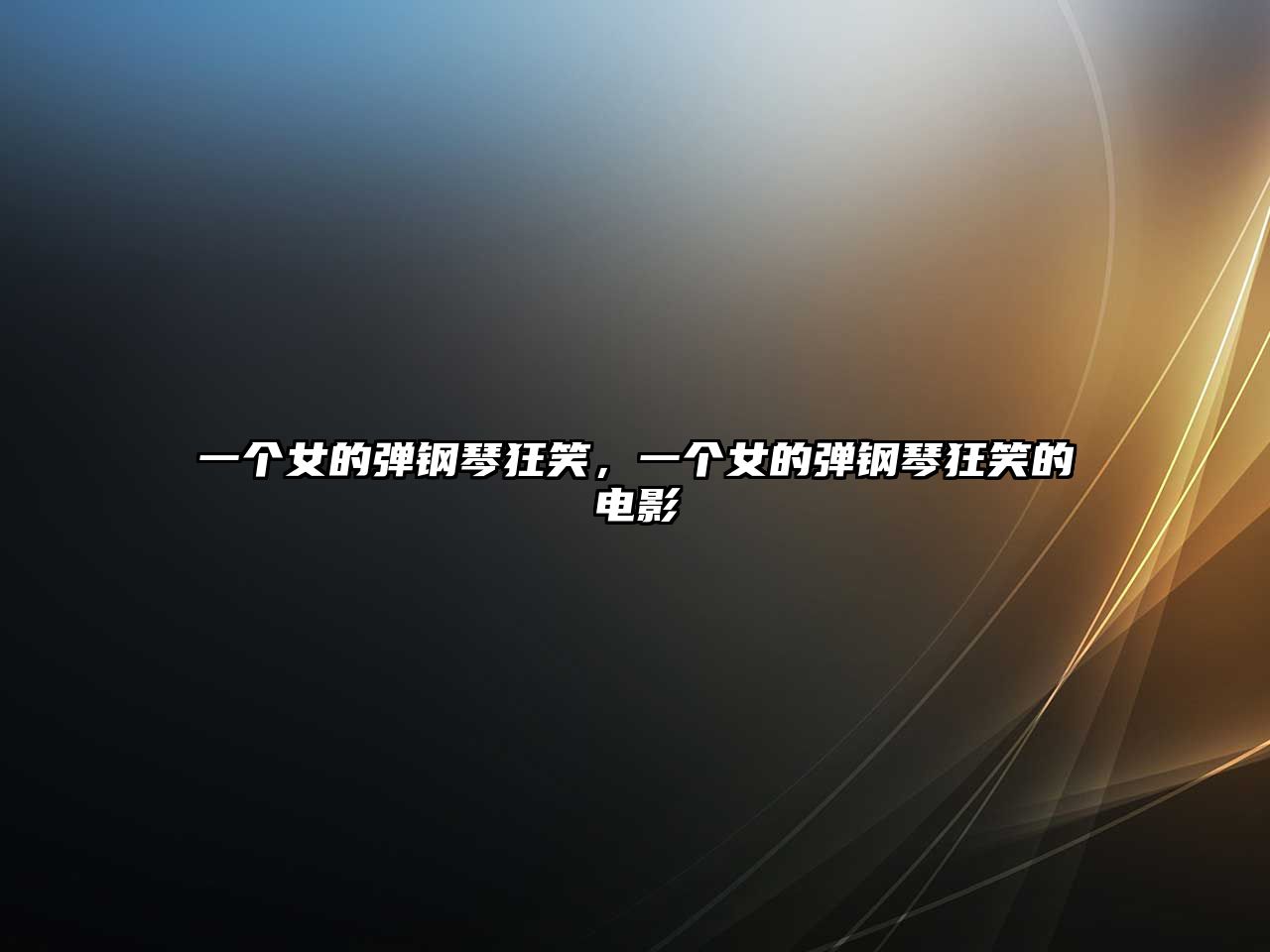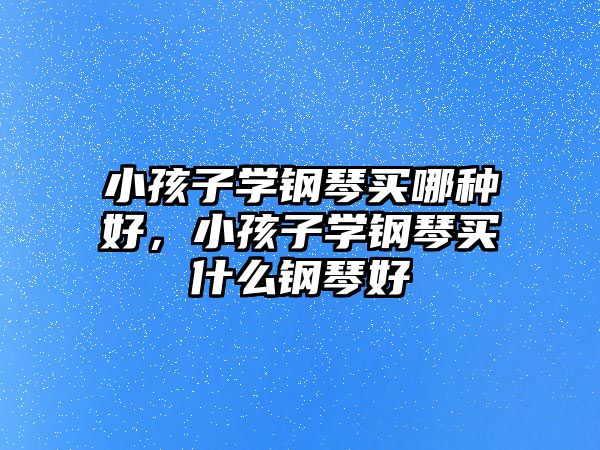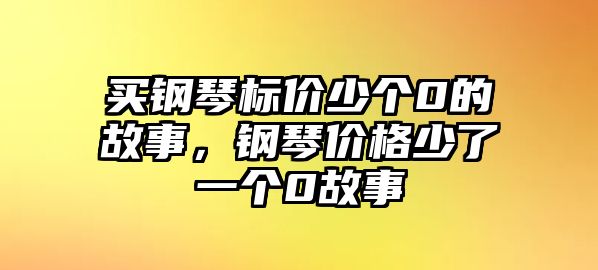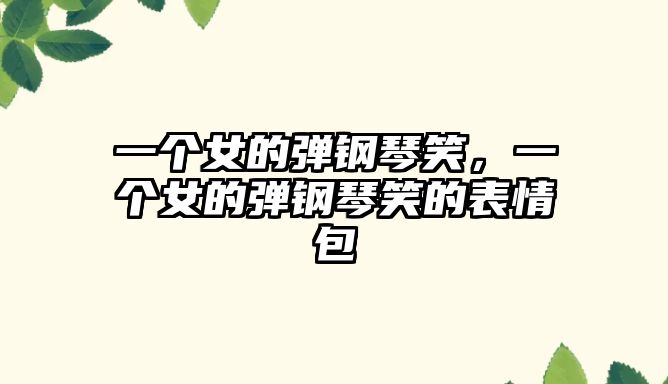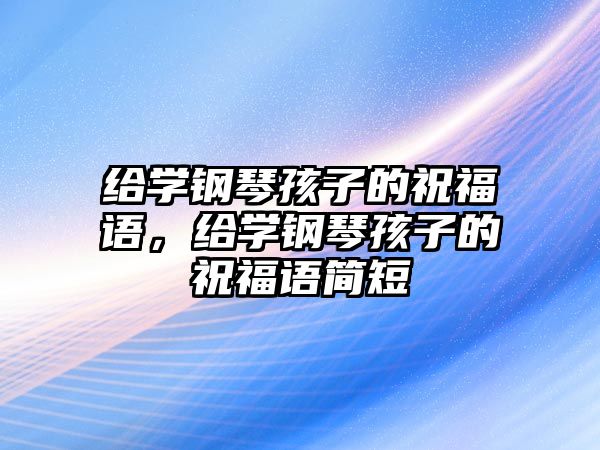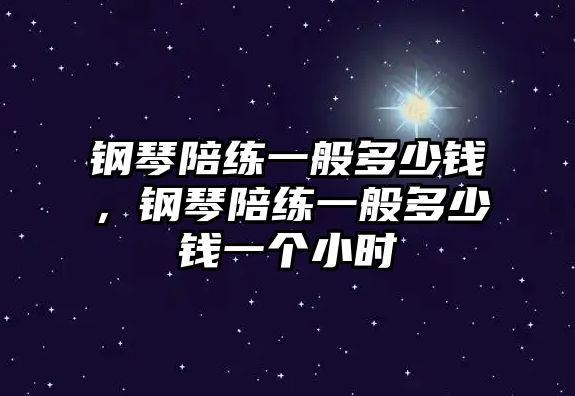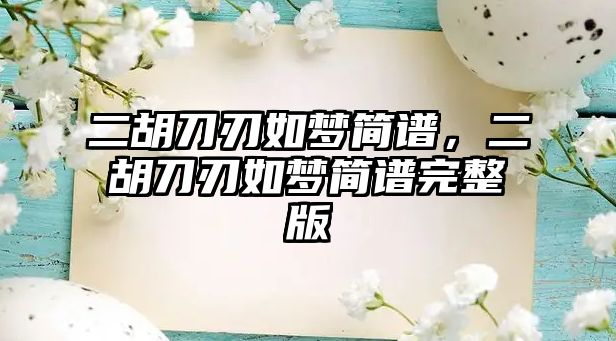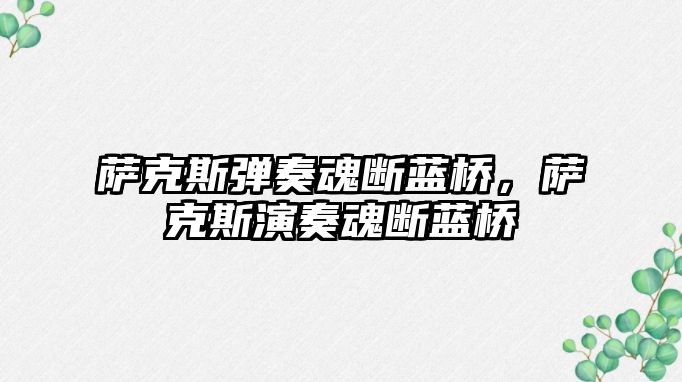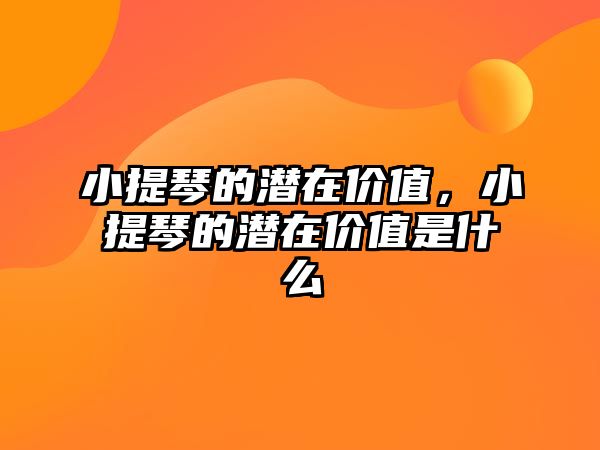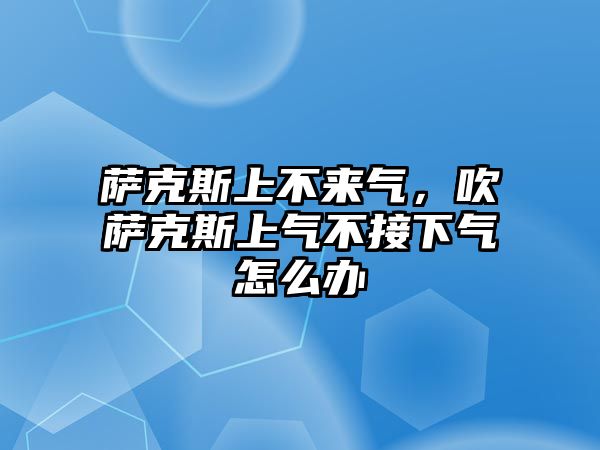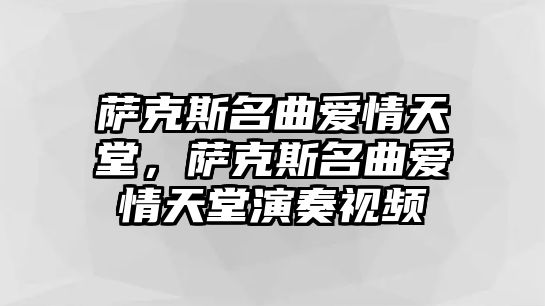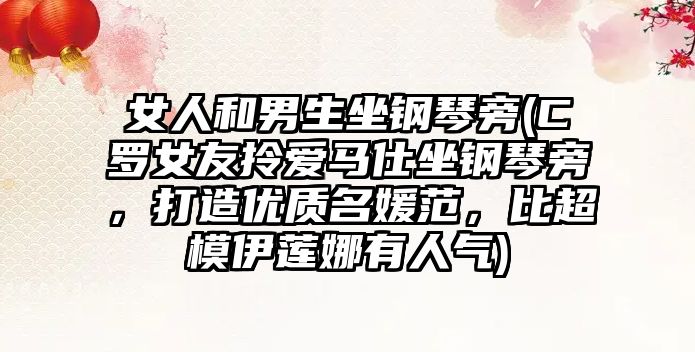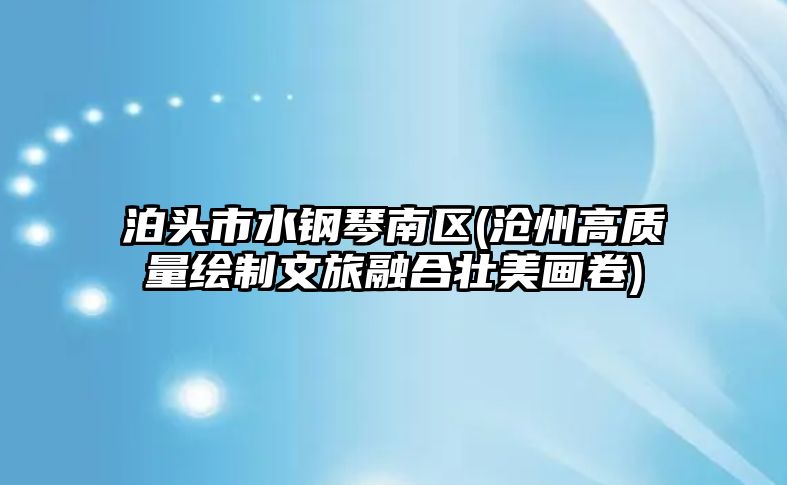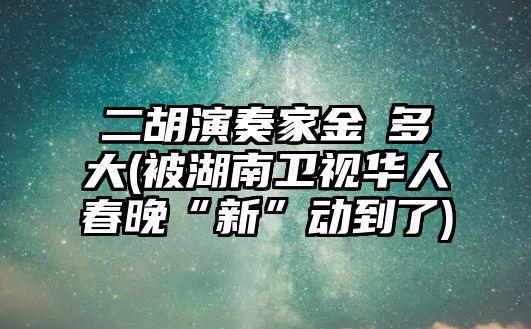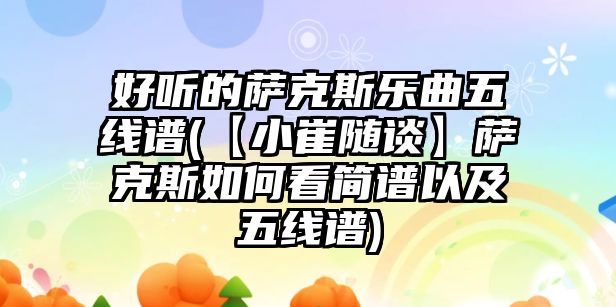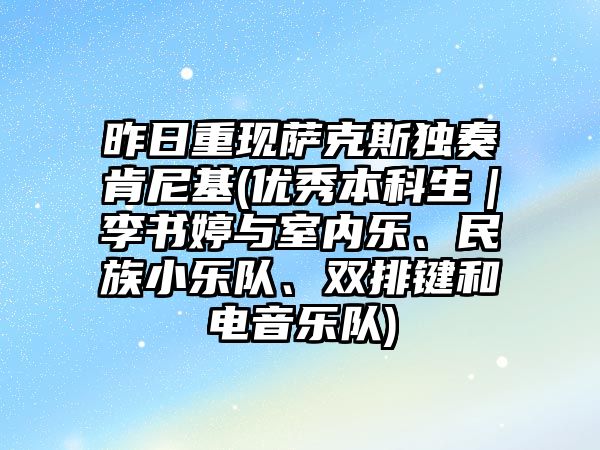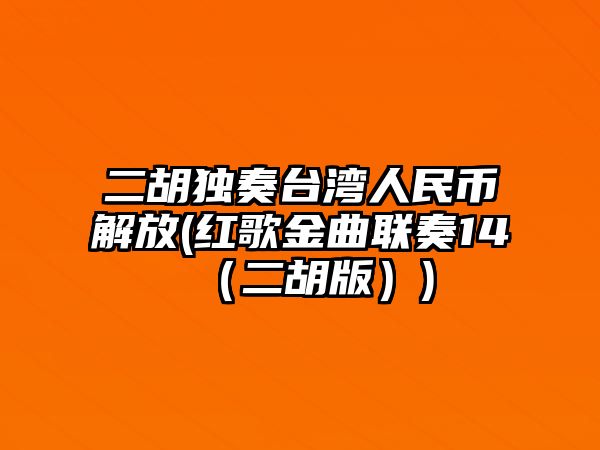薩克斯伴奏光明(離家不遠一條河)
作者:原因
車流滾滾,馬達轟鳴。走在被稱為“昆明的長安街”的廣福路人行道上,忽見行道樹的縫隙閃出一道亮光。是河,一條綠蔭遮不住的河。

真想不到,鬧市里還藏著這樣一幅幽深。說“幽”,是河岸邊這條鋪著螺紋地磚的路,被濃蔭遮覆得嚴嚴實實,滴溜溜的鳥鳴在這樹木的長廊里一聲聲婉轉回旋,釀出的卻是一管凝住的寧謐。說“深”,是一路走來都是綠墻夾道,靜若空谷,直到走得腿有些發酸。路與河依傍著,河奉獻出清澈的波光,岸奉獻出綽約的身影。
那是一個傍晚,夕陽像是被懸在河那頭的一個花籃。忽然就看見了一道紅影,從右岸的濃綠中橫過來。是一座漆得周身通紅的木橋!鳥語波光深處一道虹,有點夢幻,有點奇譎,不禁讓人揉揉眼睛后又瞪大眼睛。路邊躺臥一石塊,上書“采蓮河”三字,河里卻無蓮。它像徐志摩筆下的康河一樣,“軟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悄沒聲息地流著。
春天,夾岸的楓樹、滇樸、水杉尚未長出新葉,一兩株柳樹就垂下了綠絲絳。長亭復短亭,折柳贈別,是古人詩詞中常見的場景。但在這里,林邊的花地姹紫復嫣紅,與我告別的卻是柳絲蕩起處掠過河面的西伯利亞遠客紅嘴鷗。夏天,濃蔭如蓋,蟬鳴如泣,河水把溽熱吸個干凈后又呼出一腔清涼。秋天,河岸樹盡皆酡顏,有蚱蜢小舟輕輕搖過,劃破水中倒影,打碎了一壇壇它們高舉在手的紅酒,滿河頓時騰起烈焰。冬天,在滇池、翠湖被賞鷗人喂得胃囊鼓鼓的紅嘴鷗,有不少會飛到河里躲清靜。它們漂浮著,只是偶爾慵懶地撲扇一下翅膀或者扭擺一下脖頸,像一盞盞悠然綻放的白蓮。
歐陽修有醉翁亭,袁子才有隨園。我真是富可敵國呵,采蓮河成了我的秘密后花園。
但世上的美是藏不住的。沒過幾年,踏入這里的步履漸多漸稠,它最終成了休閑一族的打卡熱地。
很多人來這里散步:年輕情侶牽著手,腳步輕快。老兩口相扶相攙,夕陽下長長的背影,讓人久久凝視。有人來這里跑步,他們往往以外套的袖管束腰,露出短袖T恤,精神抖擻,一次次與我擦肩而過。有時,濃密樹蔭的縫隙間會橫斜出一輛輪椅,輪椅上的女人,微微瞇著波光蕩漾的眼睛,享受著陽光溫暖的撫摸。有時會有一根釣竿,一動不動地久久橫懸在河面。是因為魚餌不夠香,魚兒不愿上鉤嗎?釣竿是綠色的,酷似春天的柳枝,一只蜻蜓就盤旋著落下,輕輕地立在上面。有時,會看見三兩小孩揮舉著長竿小網在河里撈魚,撈到的卻總是一汪泥水。不遠處,一位釣魚的老人就向他們頻頻招手了。他把自己釣到的魚兒盡數分贈,孩子們雀躍歡騰。在紅木橋的那邊,有人正拍婚紗照。攝影師轉動著反光板,把陽光打在新人的臉上,快樂像即將點燃的新婚紅燭,在他們眼睛里閃閃發亮。
最是秋天,仿佛寫下紅橋這筆酣墨飽的粗重一橫時,淋漓的汁水在宣紙上漫灑開去,水杉、楓樹、滇樸洇濡著染紅了半邊天。這時節,熙來攘往均是來拍照的人。當晚霞點燃遠山之巔,睜眼閉眼都是紅光一片,一時很難分清,哪是天上,哪是紅塵人間。
這樣的生活花絮,總是在紅木橋畔拼貼出一幅幅活色生香的人間世象圖。
但這里也不乏負重的人生。
一位年輕女子,每次來到河邊,都是背一個、牽一個,推著的嬰兒車里還坐著一個孩子。對于童嬰,大自然也像母親的懷抱一樣充滿誘惑。行進在夾道的綠蔭中,牽著的孩子時常要掙脫母親的手去捉草叢里的飛蟲;背著的孩子則伸長了脖頸四處張望,口中咿咿呀呀;坐在嬰兒車里的孩子,一縱一縱,像要一頭撲進樹影波光。每次與這列母子的“方陣”相遇,我都會閃到路旁,目送他們緩慢地從身邊過去。有一天,在紅木橋邊,我看見他們想登越幾級石階上橋,就急忙上前,欲幫那年輕母親抬嬰兒車。想不到她卻語氣堅定地說,“我可以的!”她先把能走的孩子牽上木橋,然后走下石階,正一正背上的孩子,兩手抓住嬰兒車的邊框,咬咬牙,一步一步,把車抬上木橋……
這以綠蔭紅橋為背景的一幕是那么生動。她回過頭,抬手捋捋額發,對我微微一笑的一瞬,定格在我的心間。
河邊開始有人賣菜了。萵筍、蓮藕、白菜、茄子,擺放在一塊攤開的塑料布上,色彩斑斕。散步的、跑步的、攝影的,各色來這里放松放松的人,離去時也會順帶買些菜回去。謀生總是不那么容易。這些擺地攤的小販,往往天剛亮就出現在河邊,直到暮色蒼茫還在守候。昆明的氣候,四季無寒暑,一雨就成冬。即使陰雨天,依然能看到他們的身影。最難忘一個黃昏,指著面前因天冷無人問津的蔫癟青蔬,一個賣菜人嘆了口氣對我說:“最遭罪的是它們!”
世上竟有這樣的人,吃著不為人知的苦,忍著不為人知的痛,憐惜的卻不是自身,而是一抹來自土地、陽光和汗水的鮮活顏色。
不久,河岸上還出現了一個賣魚的攤點。幾個紅色的大塑料盆里,鯉魚、草魚、鯽魚在游動。湊過去看的小孩忍不住伸手摸一摸,魚便猛然擺尾激濺起一串水花。一陣哈哈大笑,來自一位頭發花白、滿臉皺紋的賣魚婦女。“來買魚呀!今天有桂花魚,獨此一家,非常經典……”有人過往,她就會大聲吆喝。“經典”?這樣的詞語出現在魚販口中,我不禁笑了。書面雅語的泛化、世俗化,是當今一個有趣的現象。桂花魚鱗殼金黃,肉質鮮嫩,我第一次買到、吃到這種魚,口舌留香。一天傍晚,我從她身邊走過,她正在收攤。偌大的塑料盆里,還剩一條魚沒賣掉。她撩起圍裙抹抹手,想了想,端起盆走到河邊,連水帶魚傾入河中,然后久久地站在岸邊,看著那條金色的身影向紅橋游去,直至不見……
疫情起起伏伏,去采蓮河邊的人隨之減少了。到得全國“闖關”成功,我才又像那條被放生的魚一樣,“游”向河邊,“游”向紅木橋。
正是初春,陽光像新釀的醪糟汁液,經河岸的扶疏枝葉過濾滴漏而下。我從菜攤前走過,一個常來跑步的人,微笑著朝我點了點頭。來散步的人中,似乎增加了一些陌生面孔,一對年輕人緊緊地依偎著,女子好像懷孕了,男子的一只手挽住或者準確點說是托住女子的腰慢慢往前走,體現出對愛和生命的悉心呵護。這個季節綠草芊芊,新花初綻,一對對拍婚紗照的年輕情侶,風姿綽約。一切都那么熟悉,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過。然而,我總感覺有什么地方不對勁。對了,一路都沒看見那個賣魚的攤點。那位有著爽朗笑聲的老人是不是到別的什么地方叫賣她的“經典”去了?我買了兩支黃瓜,順便向攤主打聽,這才知道,老人去世了。
我的心情有點沉重。往前走,在一段落葉樹夾道的河岸,遇到了三個孩子和他們的母親。大一些的孩子已經不用母親緊緊牽住手了。他向前緊走幾步又轉過身倒著走幾步,低著頭,眼睛睜得老大盯住地面。原來他是想踩自己的影子,我不禁啞然失笑。孩子正為老踩不到那比自己還頑皮的精靈而懊惱,卻聽到了母親的呼喚。他跑著追過去,被母親背著的孩子睡得正香。嬰兒車里的孩子被母親推著往前走,手里搖著一枝花,已經會“爺爺、爺爺”地叫我了。
遠處不知什么人吹奏起了薩克斯,先是舒伯特的《搖籃曲》,后是《紅樓夢》的插曲《葬花吟》。前者輕柔而憂傷,后者深沉而哀怨。串串富有色彩的音符,在河面漂流,在天空飛翔,既像漣漪中的漣漪,又像回聲中的回聲,更像一支游走的箭,一下就射中我的心房,濺起幾滴惆悵。
“每一只搖籃都在問我們
你來自何處?
每一口棺槨都在問我們
你去往何方?”
記不清是誰寫的詩了。也許,離家不遠的這條河,只是我們生命列車中的一個途經之處,可以略作流連,也有人就此下車。也許,對于有些人,在某些時候,這條河是一種撫慰;而對于另一些人,在另一些時候,它只是艱辛生活的一個支點、一個節點。
有來有去,有生有死。也許,對于人類,地球上任何值得眷戀的角落,都只是生命的一個驛站。
《光明日報》(2023年05月26日14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