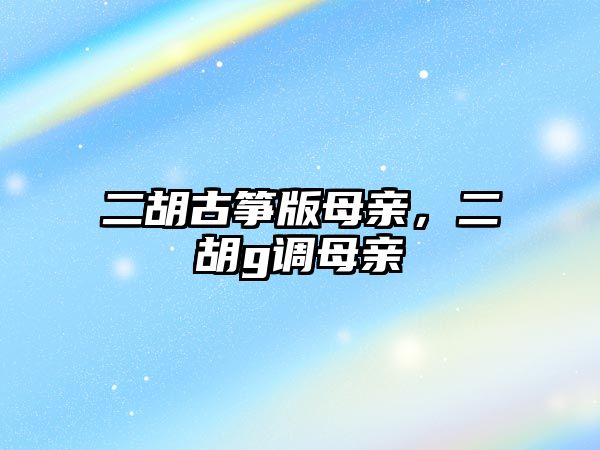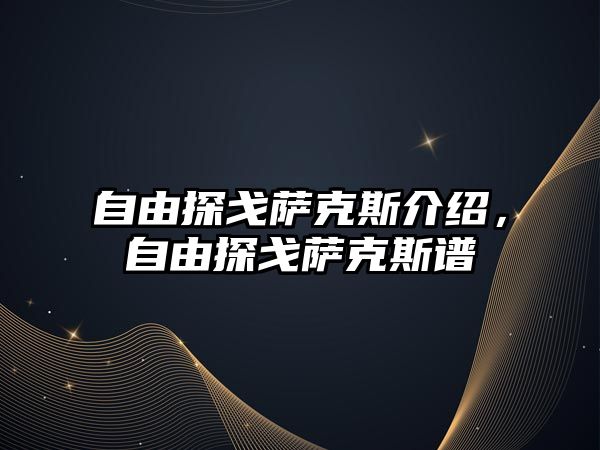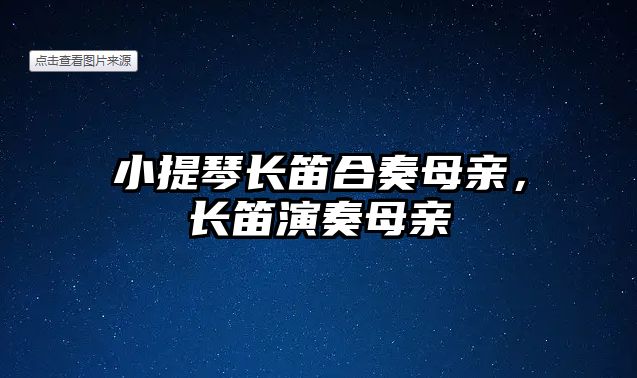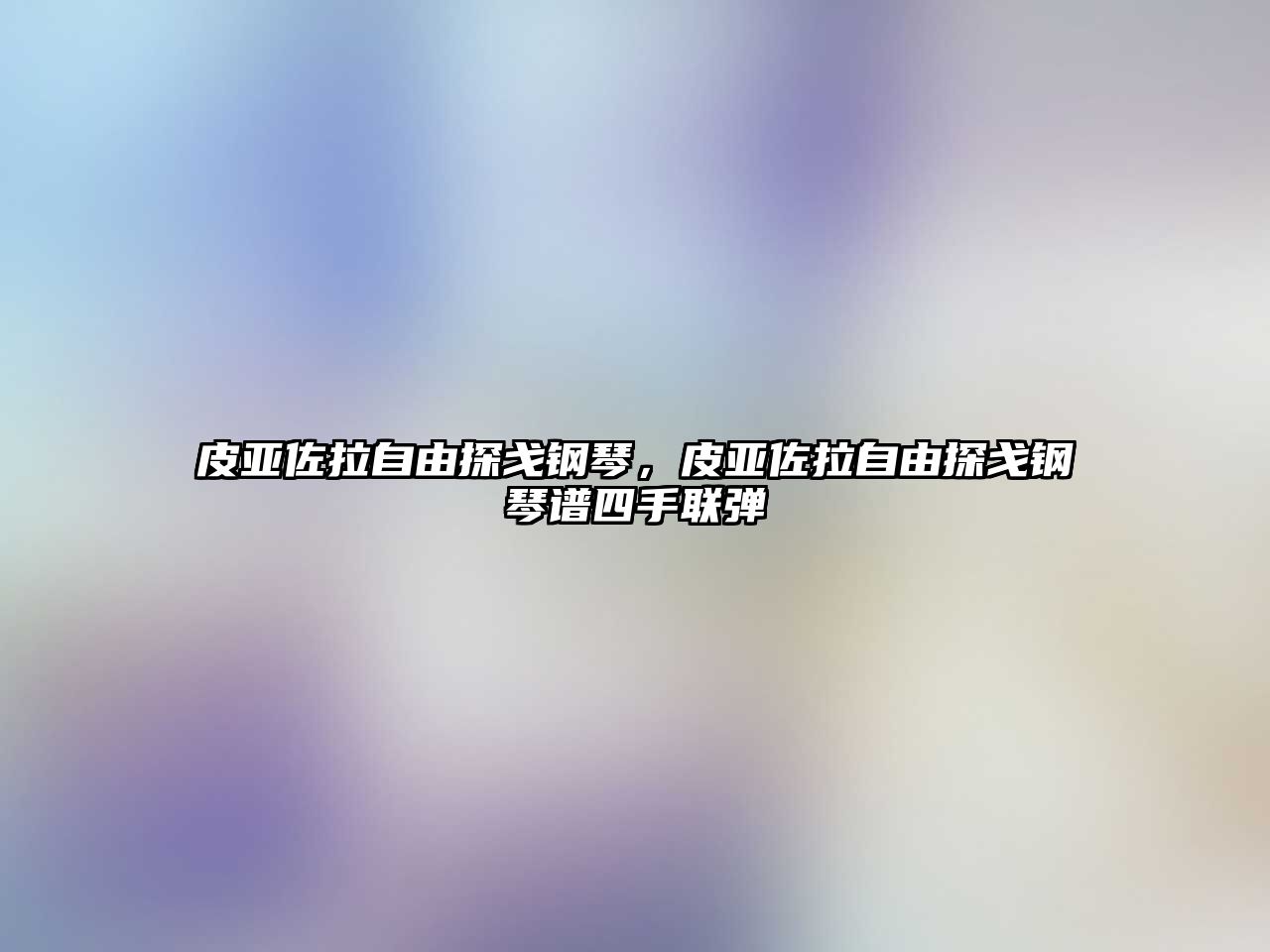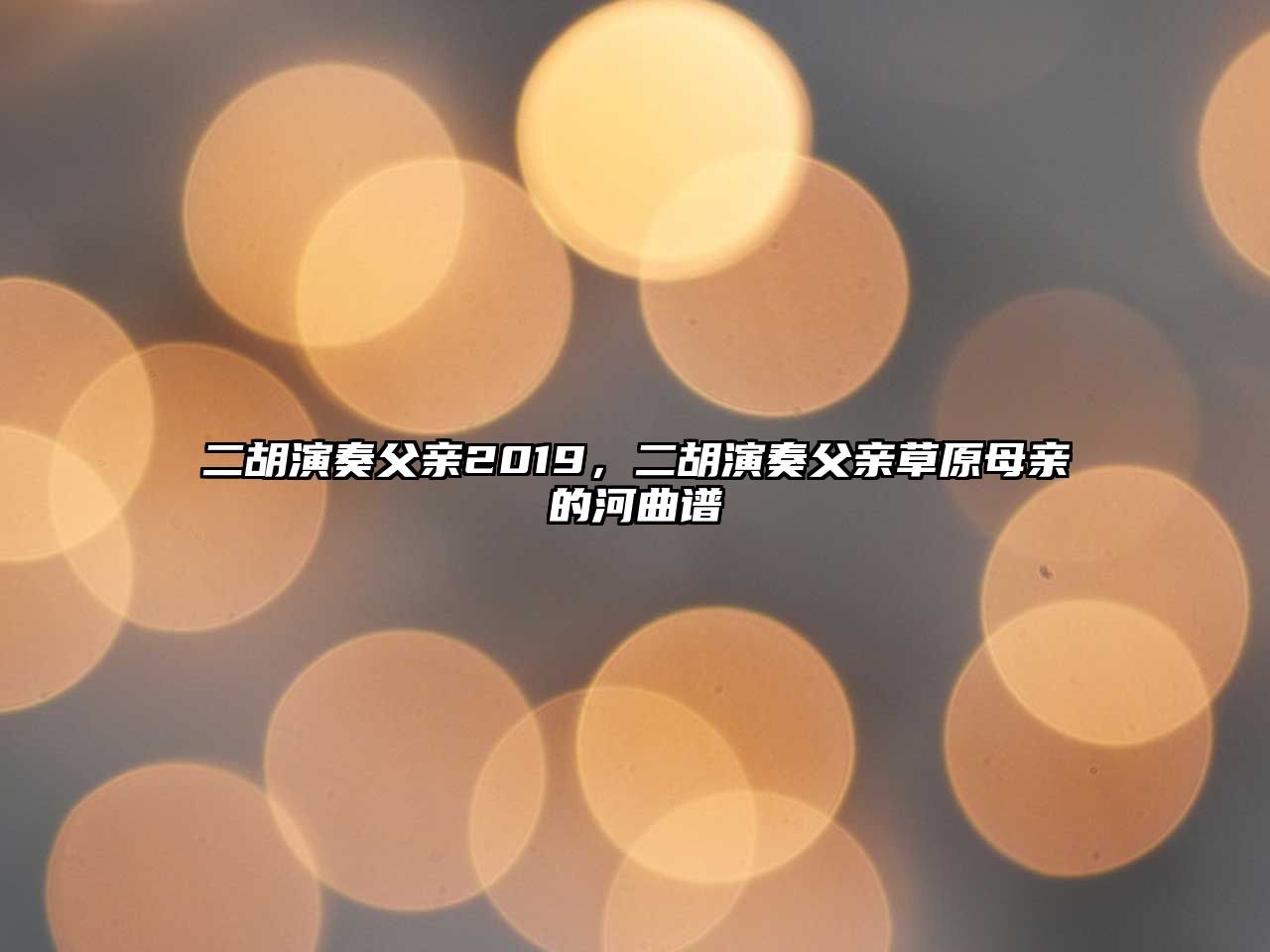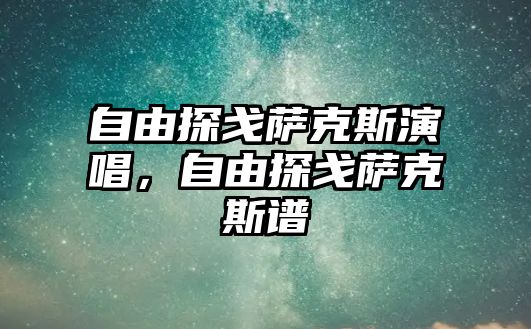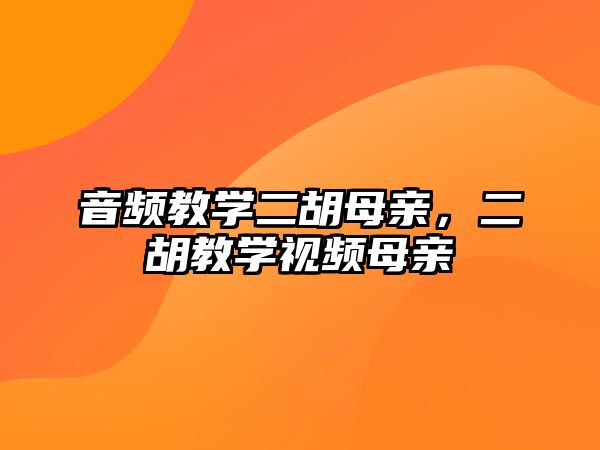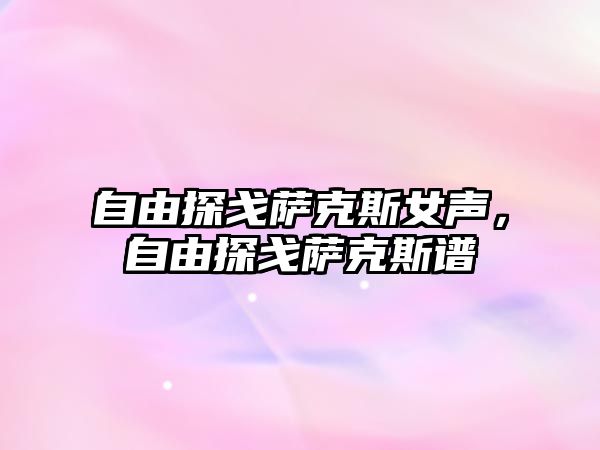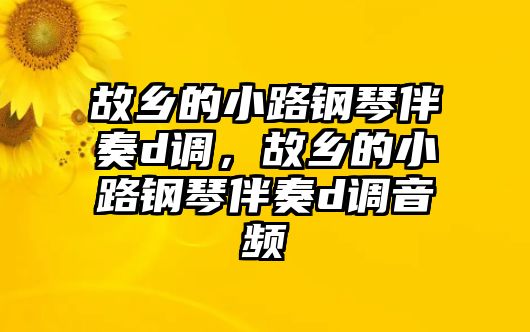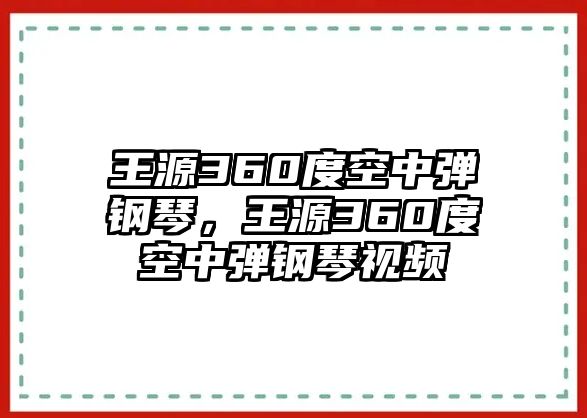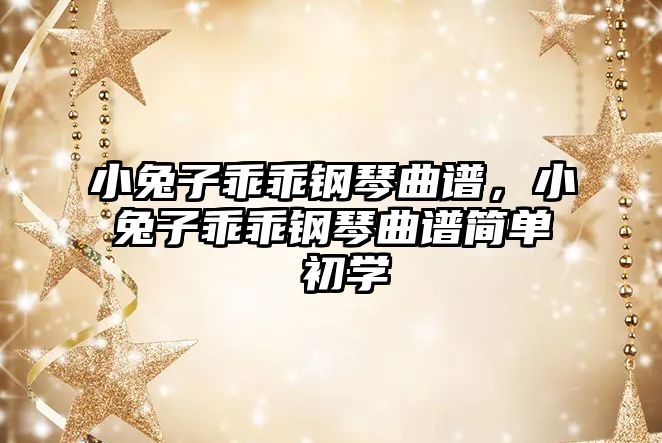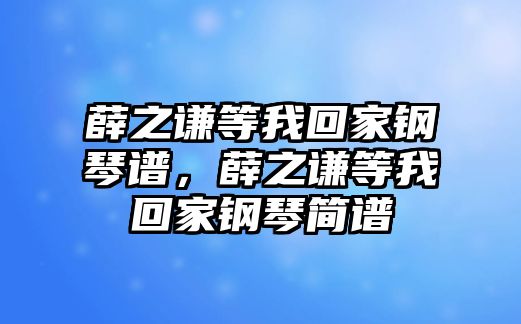大學生鋼琴老師(《鋼琴教師》:一段扭曲的師生戀情,卻是對自由的極大肯定)
文|書侃兒
一個是“性壓抑”的鋼琴教師,一個是追求刺激的大學生,兩個人扭曲病態,殘忍壓抑的愛情故事,曾是那個時代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它出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耶利內克的長篇小說《鋼琴教師》,自出版以來便飽受爭議,但時間給予了證明。

如今,“性”已不再是敏感的話題,當我們拋開低俗的欲念,透過女主人公病態的欲望,看到事情的本質后會發現,這一切都清晰地指向了一個主旨,那就是自由。
①
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埃里卡是一名鋼琴教師,她外表光鮮,氣質冷艷,是一下就能讓人肅然起敬的那種人。也可以說,一看就是一張禁欲臉。

她的私生活是極其蒼白苦悶的,四十歲了依然單身,還和母親睡在一個床上,幾乎沒怎么接觸過男人,她像一個孩子一樣接受母親的保護和控制。
有一次,她偷偷買了一件連衣裙,遭到母親的強烈訓斥,母親認為,作為一名教師,絕對不可以穿花里胡哨的裙子,何況它價格昂貴,簡直就是亂花錢。

在母親那里,她沒有一切權利,她只能按照母親規定的方式生活。所以她恨母親,恨不得母親馬上去死。同時,她又離不開母親,她已經習慣了在母親的控制下生活。
她沒有想到的是,如死水一般沉悶的生活,也會泛起陣陣漣漪。
瓦爾特是一名年輕帥氣的大學生,放假期間在埃里卡那里學習鋼琴。他生性風流,相貌英俊,喜歡刺激,埃里卡高傲冷艷的氣質深深吸引了他,于是就開啟了猛烈的追求。

埃里卡面對學生的追求是厭惡的,并一次次地拒絕了瓦爾特。可當她看到瓦爾特和其他女同學親密接觸時,又心生嫉妒,甚至還會把碎玻璃偷偷放到女同學的大衣里,以此來滿足她的報復心。
嫉妒讓埃里卡明白,她心里是渴望和瓦爾特在一起的,于是她決定接受瓦爾特的追求,但她愛的方式又是那么冷漠,生硬,毫無情趣。

多年來被壓抑著的性的本能早已扭曲變形,她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愛一個人,她沒有了愛的能力,也沒有了性的能力。
可她依然想愛,想要宣泄內心的情感,她必須死死抓住瓦爾特,那是她唯一的機會。
她給瓦爾特寫了一封信,信上是她對瓦爾特的要求。

本來嘛,女人在接受男人的追求之前,提一些小要求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兒,然而埃里卡的要求卻讓瓦爾特心生厭惡。
在信中,她表述了自己壓抑的內心和苦悶的生活,同時,她希望瓦爾特能以暴力的方式滿足她對性的渴望。

面對如此荒唐惡心的要求,瓦爾特拒絕了。他說他本來是愛她的,現在不愛了。
埃里卡更加絕望了,她親手堵上了唯一可以宣泄情感的出口,那天,她甚至想讓母親代替瓦爾特彌補她感情上的缺口。
那天晚上,她突然壓在母親身上,母親則拼命推開她,她極力想要制服母親所表現出的力量,似乎就是她對命運的抗爭。

母親就像是她的暴君,而她是母親可憐的臣民,她痛苦、壓抑、絕望、憎恨,然后帶著所有情感臣服于母親。
她憎恨強權,也習慣了強權。她的人性早已在壓抑和沉悶中扭曲了,所以她才想要異于常人的刺激,才會對愛情有那樣匪夷所思的想象。
②
在經過幾次三番的嘗試后,兩個人的愛情還是充滿腐爛的氣息。正如瓦爾特所說,埃里卡是臭的。
埃里卡越是愛瓦爾特,瓦爾特越是感到惡心,他終于決定報復她。
好吧,那就滿足你信中的要求。他用最殘忍和最惡毒的方式給予埃里卡對愛的幻想,埃里卡沒有因此得到滿足,她是痛苦的,絕望的,她沒有得到一絲快感。

唯一能改變埃里卡生活的大門已經關死了,那扭曲的欲望并非但沒有填補她人生的缺口,反而令她更加空虛。
她懇請瓦爾特不要將這件事宣揚出去,她還是那個外表光鮮,氣質冷艷,受人尊敬的鋼琴教師。

第二天,當埃里卡再次看到瓦爾特和一群女孩嬉笑打鬧時,她沒有嫉妒,也沒有激動,甚至毫無情感的拿出一把匕首,插進了肩膀。
然后,她轉身回家去了。

家,那個在母親控制下,如牢籠一般黑暗腐爛的家,是她唯一的歸宿。
這,是埃里卡最大的悲哀。
她始終無法超越自身的狹隘,也掙脫不了母親為她搭建的牢籠,她的一生,從未有過片刻自由。
③
《我的團長我的團》中有這樣一句話:“中國人,命都不要了,就要安逸,死都不怕,就要安逸。”
喬治·奧威爾的《1984》中也說:“人類有兩種選擇,幸福和自由,對大多數人而言,選擇幸福比較好。”
當然,上述兩者都是諷刺,那“不要命的安逸”和“被奴役的自由”是泯滅了人性換來的茍且偷生。
就像埃里卡一樣,即使母親死后,她依然無法擺脫母親的控制,因為她已被“強權”塑造成了固定的模樣。
自由無疑是人權中最重要的東西,歷史一次次證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旦失去自由,思想便會凝固,也注定百業不興。
埃里卡病態的半生,便是“不自由”的產物,所以我才說,《鋼琴教師》是對自由的極大肯定。